時(shí)間:2023-12-15 10:13:44
引言:易發(fā)表網(wǎng)憑借豐富的文秘實(shí)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敦煌文化的藝術(shù)特征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內(nèi)容,可隨時(shí)聯(lián)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guān)鍵詞:敦煌舞 三道彎 審美 敦煌壁畫
一、敦煌舞審美概述
敦煌舞舞姿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講究頭、肩、胸、胯、膝、踝的“三道彎”扭動,也稱“S”形。這種出肋、出胯、移腰、曲膝、勾腳的舞姿以西涼樂為基礎(chǔ),來源于敦煌壁畫上呈現(xiàn)的舞蹈姿態(tài)。在歷史的長河中,敦煌舞受到儒家傳統(tǒng)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的幻化無為的思想的不斷侵染,也融合了傳統(tǒng)的中國藝術(shù)審美中對意象的塑造思想,并且保留了其創(chuàng)設(shè)之初的浪漫氣息。敦煌舞繼承了中國唐代宮廷樂舞的傳統(tǒng),吸收借鑒西域各民族舞蹈舞姿,是多方藝術(shù)和審美觀點(diǎn)的集合,形成了曲中求圓的審美特征。
二、敦煌舞“三道彎”的審美內(nèi)涵
敦煌舞中的“三道彎”的內(nèi)涵基因深受歷史文化的影響。敦煌壁畫唐代經(jīng)變圖中有不少歌伎樂舞形象,其舞蹈造型多呈現(xiàn)為頭、肩、胸、胯、膝、足相應(yīng)的意象異向擰扭,即S形。敦煌舞中的“三道彎”的審美內(nèi)涵正是依據(jù)這種歷史文化的審美原則發(fā)展而來,并把“三道彎”統(tǒng)一于對稱、和諧的審美內(nèi)涵中,最終形成了敦煌舞獨(dú)特的風(fēng)格特征。例如,舞劇《絲路花雨》里有一個(gè)典型舞姿“反彈琵琶”,就是取自敦煌壁畫舞姿素材,是三道彎之體態(tài)的生動展現(xiàn)。敦煌舞的“三道彎”要求舞者身體的各個(gè)部分的動作往來交織,形成一個(gè)一個(gè)的三道彎。肋、胯和膝共同構(gòu)成身軀S形的三道彎,乃至多道彎的體態(tài)。敦煌舞舞姿中還有柔和、直角等態(tài)勢不同的曲線,柔和的小曲線,直角的三位體式曲線,S型大曲線等,共同構(gòu)成了敦煌舞美妙柔和的風(fēng)格特征。
三、敦煌舞“三道彎”的審美特征
在千變?nèi)f化的敦煌舞動作中最顯著的特征是“三道彎”。敦煌舞上肢、下肢都是“三道彎”,舞姿造型要講“三道彎”,人體運(yùn)動的軌跡也要體現(xiàn)在不斷變化交織的“三道彎”的輪廓之中。“三道彎”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特征既包括外層的外化形式,也包含著內(nèi)層次的審美原則,外化形式是以內(nèi)層次的審美原則為依托,并由此形成對稱的舞姿造型,使外化與內(nèi)涵相統(tǒng)一,是構(gòu)成敦煌舞風(fēng)格特征的核心。
(一)形體的藝術(shù)美
敦煌舞在形體上最大的特征是對“圓”和“曲”的追求,形成獨(dú)特的藝術(shù)美。敦煌舞與中國古典舞“圓”的審美特征完全不同。舞蹈學(xué)者在進(jìn)行敦煌舞創(chuàng)作時(shí),將敦煌壁畫“S”形的基本形態(tài)進(jìn)行了保留,并將頭、胸、胯、膝、踝構(gòu)成屈、曲的形態(tài);同時(shí)融匯儒道的傳統(tǒng)文化,將其韻律、線條、結(jié)構(gòu)和走向的棱和角,轉(zhuǎn)變?yōu)槿帷④洝⒒。扒星髨A”。敦煌舞如行云流水般展現(xiàn)人的形體的藝術(shù),將平和之氣隱于“韻”和“勢”中。
(二)形象的意象美
舞蹈是肢體語言藝術(shù),外在形態(tài)包括“形”和“象”。意象是升華和凝練的藝術(shù),作為舞蹈的外部形式,“象”是在“形”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直接給予觀眾視覺的立體感知。換句話說,舞蹈藝術(shù)外部的形象特征,離不開肢體語言、動作造型的具象性。敦煌舞蹈非常重視“意象”,有著獨(dú)特的舞蹈語匯和審美特征。敦煌舞的每一個(gè)舞姿造型,每一件服裝道具,每一個(gè)場景布置都凝練著盛唐風(fēng)光、佛教藝術(shù)和浪漫氣息,展示著唐代樂舞妖嬈迷人的風(fēng)采。
(三)虛實(shí)結(jié)合的藝術(shù)
舞蹈的意境不僅展現(xiàn)一種情景交融的場景,更可以觸發(fā)觀眾豐富的聯(lián)想和想象。所以實(shí)境和虛境組成了意境,即虛實(shí)相生成意境。實(shí)境是指舞蹈藝術(shù)家通過對生活進(jìn)行提煉,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某一特定舞姿造型;而虛境是指舞者通過舞姿傳遞給觀眾的某種思想和情緒,引起觀眾聯(lián)想和想象的意象。實(shí)境是虛境的先決條件,虛境是實(shí)境的升華,舞蹈就是虛實(shí)結(jié)合的完美產(chǎn)物。敦煌舞就是這樣,虛實(shí)相承,在圓與曲的轉(zhuǎn)換中,在中和之氣內(nèi),完成著虛與實(shí)的轉(zhuǎn)化,一時(shí)柔弱無骨,行云流水,一時(shí)又宛若蛟龍,氣息萬鈞。
綜上所述,敦煌舞的動作以“三道彎”為動作核心,并在“三道彎”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和變化而來。敦煌舞充分運(yùn)用人體的線條、節(jié)奏、律動,曲中求圓,靈活多變,形神兼?zhèn)洹6鼗臀枳⒅匾庀蟮乃茉欤鶜庥宽嶋S,以舞傳情,以情感人,而又虛實(shí)相生,意境幽美,又侵染著無盡的浪漫氣息,這些審美特征使之具有強(qiáng)烈的曲線美感和勃勃生機(jī),因而獨(dú)具藝術(shù)風(fēng)韻。
參考文獻(xiàn):
[1]成葆.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繼承和弘揚(yáng)[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2]高技.李雛.中西舞蹈比較研究[M].裕臺公司中華印刷廠,1983.
[3]金秋.古絲綢之路樂舞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
關(guān)鍵詞:敦煌;石窟藝術(shù);供養(yǎng)人;肖像畫;文化特征;考證
中圖分類號:J20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Devotees' Portraiture of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U Hong-sheng
歷史左右圖像,圖像佐證歷史。借鑒牛津大學(xué)藝術(shù)史教授Francis Haskell通過圖像來探索藝術(shù)與社會與歷史的關(guān)系的基本研究理論與方法,運(yùn)用到唐宋時(shí)期敦煌供養(yǎng)人畫像與題記的研究當(dāng)中。作為歷史資料,延續(xù)中古時(shí)代一千多年的敦煌石窟藝術(shù)規(guī)模巨大,各歷史時(shí)期的藝術(shù)圖像反應(yīng)了相應(yīng)的社會歷史。段文杰先生認(rèn)為敦煌壁畫是“形象的歷史”。馬德先生提出了“以史論窟、以窟證史”的“石窟皆史”的理論。
一、供養(yǎng)人畫像是中國特有的肖像畫
敦煌古道在歷史上曾經(jīng)是一個(gè)國際都會城市,這兒地處中西文化交流的國際通道――絲綢之路中段的關(guān)鍵地區(qū),歷史上漢武帝為東來西去的中西使者、商賈、僧侶設(shè)立了陽關(guān)和玉門關(guān)。自古敦煌便是“華戎所交”的都會,是一個(gè)復(fù)雜的多民族居住區(qū)域,除了主體居民是漢族人,還生活有面貌長相與漢人差異很大的粟特人、吐蕃人、回鶻人以及波斯人、印度人等。規(guī)模之大、歷時(shí)之長、內(nèi)容之豐富的敦煌石窟藝術(shù)是我國的國寶。敦煌石窟藝術(shù)源自印度, 輾轉(zhuǎn)傳到西域,經(jīng)敦煌向內(nèi)地傳播,在印度佛教石窟藝術(shù)中, 還沒有發(fā)現(xiàn)有紀(jì)年題記的供養(yǎng)人畫像。隨著佛教的興盛,每傳一地,形制都有所變化,石窟壁畫一度輝煌。敦煌地區(qū)石窟壁畫的內(nèi)容有佛說法圖、經(jīng)變畫、供養(yǎng)人畫像等等,對敦煌歷史研究具有重要價(jià)值。敦煌最早的十六國晚期洞窟里便出現(xiàn)有供養(yǎng)人畫像群并有榜題,最初的施主列像是結(jié)合儒家的祖先崇拜和自漢代流傳的畫祖先像之風(fēng)而成的佛教功德主畫像。在西魏時(shí)形成家族的畫像, 唐宋則發(fā)展為更為顯赫的等身大像的家廟,場面趨于宏偉, 供人似乎超過了供佛,表現(xiàn)了佛教石窟中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特點(diǎn)。
二、石窟與供養(yǎng)人
由石窟中供養(yǎng)人畫像和供養(yǎng)人題記我們知道敦煌石窟是中古敦煌地區(qū)的居民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供養(yǎng)人即敦煌石窟開鑿的出資者,又稱為施主、窟主、功德主,包括敦煌社會的上層(如吐蕃贊普及各級官員、歸義軍節(jié)度使及各級官僚、敦煌佛教教團(tuán)的各級僧官等)、下層(一般普通民眾)。供養(yǎng)人畫像幾乎在每個(gè)敦煌石窟都有繪制,一般在石窟佛壇下、石窟的甬道兩側(cè)等,多數(shù)采用立像,少部分為跪姿。從漢代建立敦煌郡開始,歷代王朝不斷向敦煌地區(qū)遷徙,敦煌碑銘贊文獻(xiàn)及《敦煌名族志》等文書有詳細(xì)的記載。如敦煌唐氏來源于山東魯國郡,宋氏來源于廣平郡,翟氏來源于上蔡和豫章郡,閻氏由太原郡遷徙而來。漢族居民基本上都是從中原地區(qū)遷徙而來的,多與少數(shù)民族通婚。敦煌文獻(xiàn)《雜抄》引《良吏傳》記載倉慈為敦煌太守“胡女嫁漢,漢女嫁胡,兩家為親,更不相奪……鄰國蕃戎,不相征戰(zhàn)。”到晚唐五代歸義軍時(shí)期,敦煌地區(qū)胡漢聯(lián)姻非常普遍,在與漢族通婚和融合的過程中, 各民族接受漢文化,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上也積極漢化,少數(shù)民族的相貌特征特點(diǎn)有所減弱(但是長相的基本特征不會消失《晉書 •四夷傳》記載大宛“其人皆深目多須”)。
三、只求神似而不求形真
作為供養(yǎng)人肖像畫,顯示面貌特征應(yīng)該真實(shí)反映其本人個(gè)性,但是事實(shí)上唐宋敦煌石窟的供養(yǎng)人像與敦煌居民實(shí)際情況相去甚遠(yuǎn),敦煌供養(yǎng)人畫像中很少體現(xiàn)出民族融合、人種上的變化。供養(yǎng)人像服飾上基本漢化,外貌上個(gè)性特征弱化,單純從供養(yǎng)人像中很難區(qū)分民族身份。從敦煌石窟所繪張議潮供養(yǎng)人像、都僧統(tǒng)康賢照、靈圖寺知藏康恒安等,很難看到還有粟特人血統(tǒng)特征(史籍中的記載如粟特人:高鼻、深目、多須),普遍表現(xiàn)為面部圓潤,慈目善眉,表情莊重虔誠。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性和時(shí)代性大環(huán)境的影響,初唐壁畫的女性造型表現(xiàn)了女子豐腴和溫情,第329窟主室東壁說法圖中跪在佛陀腳下高不盈尺的豐肥的女供養(yǎng)人,上衫下裙,席地捧花,體現(xiàn)了時(shí)代對女性外貌審美的要求。供養(yǎng)人像不強(qiáng)調(diào)個(gè)性,只求神似不求形真,突出了供養(yǎng)人的共性。敦煌莫高窟第12窟的東壁門上方繪制的著俗裝的夫婦供養(yǎng)人,據(jù)《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認(rèn)為是窟主沙州釋門都法律金光明寺主和尚索義辯的父祖輩。繪于佛龕下的十身女供養(yǎng)人除了后四身為衣飾樸素的女侍從,前六身長幼排列為主人,都是長眉細(xì)眼、圓臉小口,差異不明顯。女主人長袍窄袖,發(fā)飾花釵珠鏈,合掌持花,虔誠禮敬。供養(yǎng)人之間的區(qū)別主要是衣冠服飾、供養(yǎng)人題記標(biāo)簽,總之不管是男或是女、,是僧或是俗、是達(dá)官或是庶民,強(qiáng)調(diào)表現(xiàn)的只是這些人永遠(yuǎn)供養(yǎng)禮敬佛尊。共性的提升和個(gè)性的消失,是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像的基本特征。供養(yǎng)人外貌特征包括服飾、頭飾近似,姿態(tài)大致相同或者很相似,共性特征逐漸突出乃至占主導(dǎo)地位。似乎有千人一面之嫌(除了部分重要供養(yǎng)人像線條和色彩的變化)。曾經(jīng)提出供養(yǎng)人像千人一面觀點(diǎn)的段文杰認(rèn)為“供養(yǎng)人像,是當(dāng)時(shí)真人的肖像,也是宗教功德像。一畫就成十上百,不能不采取程式化辦法,主要表現(xiàn)其民族特征、等級身份和虔誠的宗教熱忱,盡管都有題名,但不一定肖似本人,明顯地看出來千人一面的傾向。”經(jīng)北朝隋唐五代宋代七八百年,這種千人一面的供養(yǎng)人肖像畫風(fēng)敦煌地區(qū)一直保持著。因?yàn)檠夑P(guān)系而相貌接近的家族家窟繪制的家族成員供養(yǎng)人,可以理解這種千人一面的現(xiàn)象,如翟家窟、陰家窟、令狐家窟、陳家窟、李家窟等。雖然胡漢供養(yǎng)人繪制在一起,卻看不到深目高鼻的胡人特征。實(shí)際上千人一面更多的是消除少數(shù)民族的面目特征。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審美觀是影響繪制供養(yǎng)人像的決定因素,佛教造像的很多外貌要求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也同時(shí)適應(yīng)于人像繪制。敦煌地區(qū)是一個(gè)多民族居住區(qū)域,在審美觀的形成上融合了各個(gè)民族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敦煌地區(qū)還是一個(gè)以漢族為主體的區(qū)域,漢族的傳統(tǒng)文化占據(jù)的主導(dǎo)地位,在審美觀方面更多體現(xiàn)了漢族的標(biāo)準(zhǔn),因而敦煌石窟供養(yǎng)人像不根據(jù)具體對象面貌特點(diǎn)來繪制供養(yǎng)人畫像。在十六國北朝時(shí)期受以清瘦為美的魏晉遺風(fēng)影響,而到唐代則轉(zhuǎn)變以肥胖為美,除了頭飾衣服和持具的差別,面部相貌基本沒有差別。如體現(xiàn)在敦煌石窟繪制的供養(yǎng)人中的健壯豐滿有莫高窟第231窟東壁門上陰嘉政父母供養(yǎng)像。個(gè)性服從共性,突出共性淡化個(gè)性,眾多的供養(yǎng)人像排列在一起,就很難看出之間的區(qū)別,供養(yǎng)人像圖形特征繪制得盡可能符合敦煌地區(qū)的基本審美標(biāo)準(zhǔn)。
參考文獻(xiàn):
[1]段文杰.形象的歷史――談敦煌壁畫的歷史價(jià)值[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108-134.
[2]曹意強(qiáng).圖像證史――兩個(gè)文化史經(jīng)典實(shí)例[J].新美術(shù),2005,(02):24.
[3]陸慶夫.唐宋間敦煌粟特人之漢化[J].歷史研究,1996,(06).
關(guān)鍵詞:敦煌壁畫;古典舞;敦煌舞蹈;形態(tài)特征;藝術(shù)特色
敦煌藝術(shù)是人類歷史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一大奇跡和瑰寶,舉世聞名,敦煌舞則是敦煌藝術(shù)中不可或缺的珍貴部分。自上個(gè)世紀(jì)70年代末一經(jīng)問世,就以它獨(dú)特的舞蹈藝術(shù)魅力和價(jià)值,不僅深受中國廣大觀眾的贊賞和高度評價(jià),而且走出國門巡演世界,產(chǎn)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對于敦煌舞蹈,學(xué)者們普遍一致的看法是:敦煌舞蹈是國內(nèi)民族――漢族、西部各民族和中外各國――中國、印度和中亞諸國舞蹈文化交融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敦煌舞蹈是具有一整套獨(dú)特審美特征的舞蹈語匯,它的出現(xiàn)豐富了中國古典舞的舞蹈語匯,形成了自成一體的中國古典舞流派。可以說敦煌舞的成功“復(fù)活”,是當(dāng)代中國舞蹈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性事件。
一、中國古典舞的起源、發(fā)展及流派
(一)中國古典舞的起源
中國古典舞是在民族民間傳統(tǒng)舞蹈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歷代專業(yè)工作者提煉、整理、加工、創(chuàng)造,并經(jīng)過較長時(shí)期藝術(shù)實(shí)踐的檢驗(yàn),流傳下來的被認(rèn)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義和古典風(fēng)格特點(diǎn)的舞蹈。一般來說,古典舞都具有嚴(yán)謹(jǐn)?shù)某淌健⒁?guī)范性的動作和比較高超的技巧。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都有各具獨(dú)特風(fēng)格的古典舞蹈。我國漢族的古典舞流傳下來的舞蹈動作,大多保存在戲曲舞蹈中。一些舞蹈姿態(tài)和造型,保存在我國極為豐富的石窟壁畫、雕塑、畫像石、畫像磚、陶俑,以及各種出土文物上的繪畫、紋飾舞蹈形象的造型中。我國舞蹈家從20世紀(jì)50年代開始進(jìn)行的對中國古典舞的研究、挖掘、整理、復(fù)現(xiàn)和發(fā)展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成了一套完備的中國古典舞教材,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國古典舞蹈風(fēng)格的舞蹈和舞劇作品,形成了細(xì)膩圓潤、剛?cè)嵯酀?jì)、情景交融、技藝結(jié)合的特點(diǎn),以及精、氣、神和手、眼、身、法、步完美協(xié)合與高度統(tǒng)一的美學(xué)特色。
(二)中國古典舞的流派
我國的古典舞大都是通過舞蹈工作者在戲曲和民間舞蹈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長時(shí)期藝術(shù)實(shí)踐的探索、借鑒和檢驗(yàn),流傳下來的具有一定典范意義的和古典風(fēng)格特點(diǎn)的舞蹈。它不按戲曲的規(guī)范,而是根據(jù)舞蹈的特性,按照舞蹈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及要求,把技術(shù)性的內(nèi)容轉(zhuǎn)化為藝術(shù)性的內(nèi)容。武術(shù)也是發(fā)展中國古典舞蹈的一個(gè)重要基礎(chǔ)。
敦煌彩塑和敦煌壁畫同是敦煌莫高窟造型藝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的能工巧匠們以嫻熟的技巧、高度的概括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許多造型優(yōu)美、神態(tài)生動的女性形象。其中“飛天”是敦煌壁畫中藝術(shù)成就最高,也是最受人們喜愛的部分。而以“飛天”為主要舞蹈形象的敦煌舞蹈也成為我國古典舞新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拓展我國古典舞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我國的古典舞得以更好的發(fā)展。
二、敦煌舞蹈的流派由來及其對中國古典舞的貢獻(xiàn)
(一)敦煌舞蹈的由來
被譽(yù)為“世界藝術(shù)寶庫”的敦煌莫高窟,保存了極其豐富、珍貴的舞蹈形象。舞蹈是轉(zhuǎn)瞬即逝的時(shí)空藝術(shù),在沒有古代舞蹈動態(tài)資料的情況下,那些凝固在石窟壁面的各個(gè)時(shí)代舞蹈形象,成為十分罕見、珍貴的舞蹈史料 。上個(gè)世紀(jì)七十年代以前,無論歷史文獻(xiàn)還是當(dāng)代舞蹈的記錄中.都沒有“敦煌舞”這個(gè)名稱。我國舞蹈工作者對包括敦煌壁畫在內(nèi)的莫高石窟藝術(shù)進(jìn)行系統(tǒng)研究,并以此為依據(jù),創(chuàng)造性地“復(fù)活”了壁畫上“揚(yáng)眉動”、“彈指移項(xiàng)”、“扭胯蹶臂”、“騰踏旋轉(zhuǎn)”的動人姿態(tài)。今天以“敦煌”命名的舞蹈,其直接來源是敦煌莫高窟壁畫上的大量古代舞蹈姿態(tài),它是當(dāng)代舞蹈藝術(shù)家們根據(jù)對古代敦煌壁畫舞姿的研究和受敦煌樂舞壁畫的靈感啟發(fā),“復(fù)活”和創(chuàng)作出來的一個(gè)新舞種。這些來源于敦煌彩塑和敦煌壁畫的藝術(shù)形象手姿豐富,纖細(xì)秀麗,大部分是具有典型意義的美妙的舞蹈動作。后經(jīng)舞蹈工作者經(jīng)過加工、編排,創(chuàng)作出有著自己獨(dú)特的形態(tài)特征和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舞蹈形式。
(二)敦煌舞蹈在中國古典舞中的重要性
“敦煌舞”雖歸屬于中國古典舞體系,但它卻洋溢著與中原漢民族舞蹈不同的異國、異域情調(diào),肢體多曲線,舞姿多棱角,手姿豐富,腳位富于表現(xiàn)力,眼睛傳神,是敦煌舞蹈有別于其他舞蹈的獨(dú)特之處。在追尋和重塑中國古典舞的路上,我們不必執(zhí)著于走戲曲舞蹈、武術(shù)及民族民間舞蹈這一條路;豐富的文物、古代壁畫、石窟造像和文獻(xiàn)典籍等,完全可以成為舞蹈工作者尋古探微的新來源。“敦煌舞”綜合了壁畫的各種舞姿、從不同朝代的壁畫舞姿中提煉出較有創(chuàng)新價(jià)值意義的形式,創(chuàng)建出系統(tǒng)而科學(xué)的舞蹈動作體系,推動了敦煌舞蹈的蓬勃發(fā)展。敦煌舞蹈的出現(xiàn),極大的豐富了中國古典舞風(fēng)格類型和舞蹈語匯。
三、敦煌舞蹈的形態(tài)特征及藝術(shù)特色
(一)敦煌舞蹈的形態(tài)特征
敦煌舞蹈這些來源于彩塑及壁畫中歷代的舞蹈造型后被舞蹈工作者經(jīng)過加工、編排,創(chuàng)作出有著自己獨(dú)特的形態(tài)特征和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舞蹈。敦煌舞蹈異域風(fēng)格的舞蹈元素還來源于古代盛世時(shí)期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與外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敦煌舞蹈研究專家、敦煌舞基本訓(xùn)練的創(chuàng)始人高金榮認(rèn)為,敦煌壁畫及彩塑的舞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gè)方面:1.北涼到北周的伎樂天。2.唐代的經(jīng)變畫。3.各代飛天。4.蓮花童子。5.金剛力士與天王。(這是充滿陽剛之氣的男性舞蹈造型)6.世俗舞蹈。(是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直接反映)此外,還有彩塑菩薩。她認(rèn)為,敦煌彩塑和敦煌壁畫同是莫高窟造型藝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手的形狀豐富多姿、纖細(xì)秀麗,富有中國傳統(tǒng)的古典美;2.手臂柔曼多變,手腕和肘部呈棱角;3.赤足,腳的基本形狀為勾、翹、歪;4.體態(tài)基本下沉、出胯、沖身而形成三道彎。出胯動作有兩種樣式:一種是推胯;一種是坐胯。推胯是在提胯向上推出,線條較硬,動作有力;坐胯有向前和向后的不同方向,動作柔和。總的構(gòu)成剛?cè)嵯酀?jì)、曲線鮮明的一種柔、韌、沉、曲相結(jié)合的動作特征。5.使用長綢、腰鼓、琵琶等道具而舞的形象,也是其鮮明特色之一。高金榮還認(rèn)為,前期的敦煌壁畫中的舞蹈姿態(tài),有明顯的印度舞的影響,許多動作姿態(tài)來自印度,形成了敦煌舞蹈富有特色、魅力的形態(tài)特征,也由此可見當(dāng)時(shí)中國與異域文化交流、交融的開放程度。
(二)敦煌舞蹈的藝術(shù)特色
敦煌舞蹈綜合了壁畫的各種舞姿,從不同朝代的壁畫舞姿中提煉出較有創(chuàng)新價(jià)值的形式,創(chuàng)建出系統(tǒng)而科學(xué)的舞姿,推動了敦煌舞蹈的蓬勃發(fā)展。敦煌舞蹈富有濃厚的異國情調(diào),是敦煌舞蹈有別于其他舞蹈的獨(dú)到之處。飛天幾乎成了敦煌藝術(shù)的代表和象征。以扭動的身軀表現(xiàn)飛翔的姿勢,以流暢生動的線條勾勒出輕盈的體態(tài),以飄舞而富有韻律感的裙帶表現(xiàn)出“飛行”的輕捷自如,這是飛天獨(dú)有的藝術(shù)魅力所在。
敦煌舞蹈流派的出現(xiàn)與建立,其意義不僅在于為中國古典舞整體體系增加了一個(gè)流派,而更在于它將古代傳入中原的西域舞蹈文化,形象地再現(xiàn)給我們,讓我們了解了西域舞蹈的特殊風(fēng)采,體會到古代中原文化與異域民族文化交流和交融的盛況,同時(shí)體現(xiàn)出中華民族舞蹈文化強(qiáng)大的融合力和生命力。
參考文獻(xiàn):
[1]袁光明.《敦煌壁畫中飛天之研究》[M].2003年
[2]劉靖著.《敦煌藝術(shù)產(chǎn)生的文化背景》[M].蘭州西北師院學(xué)報(bào)編輯部1990年1月
[3]范興儒.《敦煌飛天》[J].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1版
[4]高金榮.《敦煌舞蹈》[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3年
[5]劉曉天.《敦煌飛天》[M].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2年5月1日
[6]陳玨.《敦煌莫高窟及周邊石窟》[M].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1日
[7]周大正.《敦煌壁畫與中國色彩》[J].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0年,7第1版
[8]高金榮.《敦煌石窟舞樂藝術(shù)》[J].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6第1版
[9]董錫久.《敦煌舞蹈》[M].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2年
[10]王克芬.《敦煌「舞譜殘卷探索》[J].新疆藝術(shù)期刊1986年1月刊出
[11]劉慧芬.《唐代樂舞研究之五》[J].故宮文物月刊第,58號第五卷第十期民77年1月
[12]鄭汝中.臺建群主.《中國飛天藝術(shù)》[M].安徽美術(shù)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作者簡介:
關(guān)鍵詞:敦煌壁畫;現(xiàn)代設(shè)計(jì);多維視覺呈現(xiàn)
敦煌壁畫是指世界文化遺產(chǎn)———中國敦煌石窟內(nèi)壁的繪畫藝術(shù)作品。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與精湛的表現(xiàn)手法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國佛教美學(xué)文化中的藝術(shù)瑰寶與文化典范。敦煌石窟藝術(shù)體系作為人類文明史上的物質(zhì)和精神財(cái)富,不僅是研究唐代政治體制、經(jīng)貿(mào)發(fā)展及的重要參考資料,還為當(dāng)前面對人們多樣性審美需求的現(xiàn)代設(shè)計(jì)者提供了寶貴的創(chuàng)作素材和靈感,有利于增加現(xiàn)代設(shè)計(jì)作品的文化厚度,實(shí)現(xiàn)經(jīng)典傳統(tǒng)文化的活化繼承與弘揚(yáng)。
一、敦煌壁畫的歷史淵源與演變
(一)敦煌藝術(shù)的源起
西漢時(shí)期,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而敦煌地接西域,使得西域的文明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促進(jìn)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東漢時(shí)期,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其眾多的信徒和自身廣泛的影響力使佛教文化藝術(shù)在中亞一帶的絲綢之路上得以傳播推廣。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交通樞紐。印度及本土高僧常聚集此地講經(jīng)說法,由此產(chǎn)生了佛教文化藝術(shù)的萌芽。隋唐時(shí)期,中央政府加強(qiáng)了對西北敦煌等地的管控,使之與長安等中原都市的來往變得頻繁,并使異域文化得以傳播。在此背景下,佛教為了自身生存開始從多角度適應(yīng)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宣傳推廣自身的基本思想。唐代在開放的政治體制的加持下,對外經(jīng)濟(jì)交流與文化輸出勢頭空前高漲。而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外交要塞,多種文明匯聚于此,使得佛教藝術(shù)向東傳播并與內(nèi)地風(fēng)俗及藝術(shù)風(fēng)格實(shí)現(xiàn)多維融合。敦煌藝術(shù)集諸多中外美學(xué)思想于一體的地域特征也就此形成。
(二)敦煌壁畫風(fēng)格的發(fā)展演變
敦煌壁畫以具象通俗的形象進(jìn)行呈現(xiàn),人物形態(tài)豐富生動,充滿著濃郁的生活氣息。敦煌五百多個(gè)石窟中主要包含有佛像畫、佛教故事畫、傳統(tǒng)神怪畫、經(jīng)變畫、供養(yǎng)人畫像等幾大類。在一千多年的演變中,佛教壁畫藝術(shù)隨著傳統(tǒng)繪畫技法的不斷變化而呈現(xiàn)出風(fēng)格多樣、時(shí)代特性鮮明的特征。在十六國和北魏時(shí)期的敦煌壁畫中,可以看到,畫師受西域壁畫的影響,以本土線描為基礎(chǔ),充分吸收外來佛教形象及色彩的表現(xiàn)手法,用蒼勁有力的細(xì)線勾勒出較為夸張的人物動態(tài)形象,以赭紅色為底,以散花圖案為背景,創(chuàng)作出254、257、275等窟的壁畫,整體畫面充斥著強(qiáng)烈的西域佛教情感繪畫風(fēng)格。西魏時(shí)期,畫師們將神仙形象及佛教形象并列呈現(xiàn)在石窟壁面之上,用遒勁瀟灑的線描加明快的色彩覆以白粉鋪地的背景之上[1],以傳統(tǒng)手繪形式表現(xiàn)高深的法義及美好的生活情節(jié),其中第249、285窟等代表了此時(shí)期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北周時(shí)期,壁畫大體是佛法故事及大型本生連環(huán)畫,白壁為底,線描勾勒,造型洗練,色彩清淡雅致,如290、428、299窟等。壁畫上的部分人物造型仍保持著西域繪畫遺風(fēng),在繪制人物肌膚之時(shí)略作立體暈染,但整體而言北周時(shí)期人物面相渾圓、身體豐壯的風(fēng)格代替了西魏時(shí)人物的“秀骨清像”之感[2],頗具中原繪畫視覺之態(tài)。唐代的繁盛發(fā)達(dá)使敦煌壁畫發(fā)展到達(dá)極盛時(shí)期。畫師們受到以長安為中心的中原地帶所流行的風(fēng)格影響,在元素題材的選擇上更加注重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寫實(shí)表達(dá),使用了大量不同的創(chuàng)作題材,創(chuàng)作出豐富生動的形象,其畫面色彩呈絢爛富麗之感,可見賦彩、渲染技巧已發(fā)展到一定高度。唐代敦煌壁畫的發(fā)展不僅反映了其開放制度下的繁榮昌盛,還標(biāo)志著具有鮮明民族風(fēng)格和中國特色的佛教藝術(shù)已然形成。宋代時(shí)期佛教逐漸衰微,因此壁畫少豪邁壯闊的場面,并且線描的用筆比較拘謹(jǐn),描繪社會生活內(nèi)容的題材逐漸減少。敦煌藝術(shù)也由此走向衰落。
二、唐代敦煌壁畫的藝術(shù)呈現(xiàn)
(一)敦煌壁畫的人物表現(xiàn)
唐代敦煌壁畫人物形象的塑造體現(xiàn)了多元文化的相互吸收與融合,人物形象逐漸由印度式、希臘式的風(fēng)格向中國式的風(fēng)格轉(zhuǎn)變。例如我們熟知的壁畫中的飛天形象。天女們在天上自由自在、衣帶飄飄的樣式美感,與西方神話畫中的需要靠翅膀飛行的“神”不一樣。在中國古代人民的認(rèn)知中,“神”是無所不能的,不需要借助任何外物飛行。飛天形象成為敦煌人物畫藝術(shù)的代表,在近五百個(gè)洞窟中幾乎都有該形象的存在。另外,唐代敦煌壁畫人物存在由原有的西域佛教形象逐步漢化的趨勢,所以菩薩畫像多具有高髻、面白素、眉毛彎長等特點(diǎn),并且受當(dāng)時(shí)審美的影響,其形象從男性化逐漸變?yōu)榕曰w型也變得較為豐腴。同時(shí),畫師們運(yùn)用豐富的色彩與精煉的線條刻畫出不同人物的行為舉止,表現(xiàn)其不同的內(nèi)心活動,使畫面變得生動有趣,深入觀者心靈。其中,供養(yǎng)人畫像是壁畫人物畫像中一種特殊的存在,是佛教信徒為修建功德自我示意的畫像,是最廣泛的社會群體功德像。人物形象表現(xiàn)比較本土化、世俗化,其主要有高僧、達(dá)官顯貴、平民百姓,這些人物體型大多比較豐滿,以顯示當(dāng)時(shí)經(jīng)濟(jì)之富足[3]。比如以凈土為主題的人物畫像,表現(xiàn)的是古代人民美好的愿望,即人們希望過上錦衣玉食、幸福美滿的生活。這些壁畫有助于研究當(dāng)時(shí)人們的服飾特點(diǎn),有著極高的歷史參考和藝術(shù)價(jià)值。
(二)敦煌壁畫的山水意境
唐朝時(shí)期流行的青綠山水在敦煌壁畫中的山水畫上也有呈現(xiàn)。以第148窟的經(jīng)變畫為例,眾多的人物圍繞在堆放舍利的臺前,背景的上部山勢在遼遠(yuǎn)的原野后面表現(xiàn)得十分雄奇,危崖聳立,并且半山腰被白云遮住。畫面上部,橙黃色的彩云與青綠重彩的山巒相對,宛如殘陽之上的晚霞,具有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整個(gè)畫面中人物故事情節(jié)與氣勢雄偉的山水所拉開的空間關(guān)系完美結(jié)合,無論在顏色表達(dá)上還是在形式構(gòu)圖上都體現(xiàn)出相當(dāng)高的水準(zhǔn),實(shí)屬佛教題材不可多得的山水佳作。唐代壁畫的山水意境不僅具有圖解故事的深邃,更是創(chuàng)作者運(yùn)用高超的藝術(shù)技法使畫面具有雄偉壯闊之美的一種體現(xiàn)。
(三)敦煌壁畫的植物裝飾圖案
唐代敦煌壁畫是基于當(dāng)時(shí)人們豐衣足食的盛世背景創(chuàng)作的,除了表現(xiàn)古人對象征力量的動物和自然現(xiàn)象的崇拜、敬重之情外,畫師們還把目光投向象征多子多福或充滿情調(diào)的葡萄、石榴、牡丹、蓮花等這些能喚起人們諸多情感的植物圖案。對壁畫植物圖案的創(chuàng)作也不再滿足于簡單明快的表現(xiàn),在藝術(shù)造型上更加追求豐富性和精致化,以映射唐代人民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富足。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畫師逐步將抽象幾何圖案和花鳥圖案融入畫面,圖案整體繁縟精致。
(四)敦煌壁畫的色彩韻味
敦煌壁畫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也離不開色彩的多樣化呈現(xiàn)。常書鴻認(rèn)為初唐色彩古樸拙稚,盛唐色彩金碧輝煌,整體而言唐色彩又呈現(xiàn)出富麗的特征。段文杰認(rèn)為唐前期色彩絢麗奪目,后期則清新淡雅、渾厚溫潤[4]。總之,唐代敦煌壁畫色彩豐富、細(xì)膩而富有感染力。初唐與盛唐兩個(gè)時(shí)期是整個(gè)唐代敦煌壁畫最豐富多彩的時(shí)期,壁畫以大戟、朱砂、猩紅、石綠、土黃等看起來較為干凈明快且華麗富足的色彩為代表,給人端莊華美之感;而到了中唐時(shí)期,壁畫的色彩褪去了繁雜富麗,以石綠、土紅為主,種類較為單一;唐末時(shí)期則是以石綠、淺土黃、土紅、赭石色為主色調(diào),無論是壁畫造型還是裝飾色彩都褪去浮華,具有溫潤如玉、沉穩(wěn)大氣的風(fēng)格。畫師運(yùn)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現(xiàn)不同的寓意,運(yùn)用這些具有極強(qiáng)視覺效果的色彩,夸張地表現(xiàn)了所要表達(dá)的思想內(nèi)容,充分表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人們的崇拜與向往之情。
三、敦煌壁畫的視覺呈現(xiàn)與現(xiàn)代設(shè)計(jì)的情感訴求
(一)敦煌壁畫的視覺呈現(xiàn)
敦煌壁畫蘊(yùn)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yùn)與豐富的宗教藝術(shù)情感,這都源于敦煌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地理環(huán)境,其是當(dāng)時(shí)各種宗教、文化、商貿(mào)活動所交匯碰撞出的藝術(shù)奇葩,是唐代多種思想文化交流融合的產(chǎn)物,是儒、釋、道文化的合璧與歷史發(fā)展趨勢。壁畫中的菩薩、天女、金剛力士等形象與宗教故事正是佛家文化思想的體現(xiàn),可以從飛天不受約束之精神中解讀出老子的政治自由以及莊子的精神自由,而壁畫中的禮樂傳統(tǒng)以及倫理道德的教化又是儒家思想的體現(xiàn),可見壁畫中蘊(yùn)藏著多元化的傳統(tǒng)文化內(nèi)容。“天衣飛揚(yáng),滿壁風(fēng)動。”這是對敦煌飛天這一繪畫形式的高度評價(jià),其再現(xiàn)了藝術(shù)的生命力以及自由之精神。菩薩、天女、供養(yǎng)人等形象姿態(tài)靈動、鮮活生動;紋樣、建筑、環(huán)境具有對稱和諧、剛?cè)岵?jì)的特點(diǎn),充分體現(xiàn)出當(dāng)時(shí)人們追求自由、充滿幻想的情感訴求,以及當(dāng)時(shí)的文人、藝術(shù)家對壓抑人性的綱常倫理、社會制度的反抗。唐代不同時(shí)期的敦煌壁畫創(chuàng)作體現(xiàn)出不同的時(shí)代精神風(fēng)貌與情感鏈接。在唐初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shí)期內(nèi),唐朝與鄰國的沖突不斷,邊患嚴(yán)重,因此在當(dāng)時(shí)崇尚軍功的背景下,壁畫中仍有不少表現(xiàn)戰(zhàn)爭的題材。盛唐時(shí)期國家統(tǒng)一,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高度發(fā)達(dá),對外交流頻繁,是唐朝的高峰時(shí)期。唐朝的繁盛,使得這一時(shí)期的人們更加注重對衣、食、住、行、游、玩等方面的追求,并崇尚自由開放,這一點(diǎn)可以從敦煌壁畫中得到相應(yīng)證實(shí)。
(二)現(xiàn)代設(shè)計(jì)的情感訴求
敦煌壁畫是敦煌藝術(shù)的精髓,是中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獨(dú)特的精神文化形式彰顯出神秘的藝術(shù)魅力及感染力。在信息時(shí)代的今天,世界各國文化交流頻繁,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與傳承也面臨著一定的挑戰(zhàn),越來越多的當(dāng)代設(shè)計(jì)師懷揣著對傳統(tǒng)文化的敬畏之心、喜愛之情,以傳統(tǒng)文化為根基,以樹立文化自信為己任,將傳統(tǒng)文化合理地運(yùn)用于設(shè)計(jì)作品中,使傳統(tǒng)文化得以傳承創(chuàng)新,引領(lǐng)設(shè)計(jì)發(fā)展新趨勢。敦煌壁畫有著極為豐富的文化符號。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現(xiàn)代設(shè)計(jì)師們開始積極關(guān)注敦煌藝術(shù),并參與了對敦煌壁畫元素的現(xiàn)代化再設(shè)計(jì),將其廣泛應(yīng)用于設(shè)計(jì)領(lǐng)域。通過對敦煌壁畫的深度分析研究,將其中的圖形、紋樣、色彩等元素進(jìn)行解構(gòu)再創(chuàng)新,從而不斷構(gòu)思創(chuàng)意并設(shè)計(jì)出既具有時(shí)代特點(diǎn)又符合當(dāng)今審美的優(yōu)秀作品。例如人們所熟知的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吉祥物之一福娃歡歡,其火焰頭部紋飾就來源于敦煌壁畫中的紋樣,彎曲回旋的線條配以鮮明的色彩,使得福娃整體形象更加生動且富有個(gè)性張力。同時(shí),敦煌壁畫中的火焰紋也有著神圣、威嚴(yán)的含義,其蘊(yùn)含著設(shè)計(jì)者對傳統(tǒng)文化的敬畏之意,有助于通過設(shè)計(jì)作品增強(qiáng)人們的文化自信。在現(xiàn)代室內(nèi)設(shè)計(jì)中,敦煌壁畫的精美紋樣也為設(shè)計(jì)者提供了豐富的設(shè)計(jì)靈感。比如,敦煌藻井紋樣衍生于古代建筑屋頂?shù)姆骄Y(jié)構(gòu),是通過特殊組合把圖案拼接在一起形成的獨(dú)特的紋樣圖案,藻井一般位于室內(nèi)的上方,呈傘蓋形,上面的圖案美輪美奐[5]。藻井圖案是敦煌圖案中的經(jīng)典且應(yīng)用領(lǐng)域廣泛,比如,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天花板和門楣裝飾就主要來源于敦煌壁畫中的藻井紋樣,其紋樣與建筑結(jié)構(gòu)巧妙結(jié)合,給人以莊重、嚴(yán)肅、華美之感。同時(shí),藻井紋也表達(dá)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設(shè)計(jì)理念。在服裝設(shè)計(jì)方面,裝飾圖案的設(shè)計(jì)應(yīng)用與服裝樣式、材質(zhì)、色彩的選擇同樣重要。當(dāng)代一些服裝之所以能夠受到人們青睞,并不只是因?yàn)槠涓S潮流趨勢的設(shè)計(jì)樣式,對傳統(tǒng)文化元素的巧妙運(yùn)用也能使服裝展示出不一樣的視覺效果。敦煌壁畫作為經(jīng)典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其豐富多樣、寓意深厚的裝飾紋樣被越來越多的設(shè)計(jì)師青睞并運(yùn)用于服裝設(shè)計(jì)領(lǐng)域。例如在法國巴黎“畫壁·一眼千年”時(shí)裝秀中,服飾選取敦煌紋樣中的大蓮花紋作為胸口主視覺圖案裝飾,其和服裝的面料、設(shè)計(jì)款式相統(tǒng)一,從而形成一種古樸、素雅、具有民族風(fēng)格的審美效果。同時(shí)這些作品展現(xiàn)了敦煌東方服飾的千年文明,透露著設(shè)計(jì)師對敦煌藝術(shù)的喜愛之情。
四、結(jié)語
絢爛多姿的敦煌壁畫是多元文化的集中呈現(xiàn),其豐富性、交叉性、多元性的視覺藝術(shù)令世人震撼,是中華民族極其寶貴的藝術(shù)文化財(cái)富,值得后人懷著虔誠之心去深度挖掘它的各種特殊價(jià)值,為現(xiàn)代設(shè)計(jì)提供了研究基礎(chǔ)與創(chuàng)意靈感,有助于設(shè)計(jì)者更好地依托非遺文化為現(xiàn)代人的生活服務(wù),同時(shí)賦予了現(xiàn)代設(shè)計(jì)更多的文化性與厚重感,豐富了現(xiàn)代設(shè)計(jì)的情感表達(dá)。
參考文獻(xiàn):
[1]杜星星.唐代敦煌壁畫色彩的觀念體現(xiàn)、視覺呈現(xiàn)與情感表達(dá)[J].敦煌學(xué)輯刊,2021(1):115-128.
[2]張?jiān)浦?路倩.“唐風(fēng)”及唐代敦煌壁畫的人物風(fēng)格[J].蘭臺世界,2013(36):149-150.
[3]鄧紅霞.敦煌壁畫的平面構(gòu)成特征及其在現(xiàn)代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J].中國包裝,2015(2):34-36.
【關(guān)鍵詞】敦煌藝術(shù);動畫;傳承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12-0182-01
敦煌文化遺產(chǎn)是中國藝術(shù)史上的一塊瑰寶,融合佛教、儒道及多種藝術(shù)為一體,體現(xiàn)出極高的思想境界和藝術(shù)境界。我國近幾年的動畫作品中,一些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形式基本消失,所以在開發(fā)敦煌壁畫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考慮能否通過動畫形式將敦煌藝術(shù)很好地傳遞給更多人。
一、敦煌藝術(shù)在動畫中的再生
動畫藝術(shù)與敦煌藝術(shù)有諸多相似性。動畫主要利用視覺符號進(jìn)行信息傳達(dá),設(shè)計(jì)者將虛擬概念轉(zhuǎn)變?yōu)橐曈X符號形式的過程,即對視覺元素進(jìn)行拆分、組合、設(shè)計(jì)、布局的一系列過程,這就會涉及我們通常在動畫設(shè)計(jì)中的造型風(fēng)格、色彩構(gòu)成等元素。[1]
(一)劇本創(chuàng)作素材。1.原型故事類。這類動畫片的劇本取材于敦煌壁畫故事,如動畫作品《九色鹿》,源于莫高窟257窟中的壁畫,該壁畫人物形象表現(xiàn)并不多,其核心在于傳達(dá)故事進(jìn)展。動畫需要將每一段核心內(nèi)容加入銜接部進(jìn)行故事改編,使之具有故事的連續(xù)性和邏輯性。2.意象故事類。動畫劇本創(chuàng)作是建立在表達(dá)對敦煌文化精神的崇敬之情上的,表現(xiàn)對佛教文化及生活的神往與想象。這類動畫劇本均無明顯的敘事要素,不以起承轉(zhuǎn)合作為要求,而是以凸顯意境為先。3.原創(chuàng)故事類。這類動畫創(chuàng)作以敦煌歷史文化為題材,或改變故事本身的時(shí)間空間,或?yàn)樵凸适录尤霑r(shí)代元素,較大篇幅地改編古代敦煌文化中的信息。
(二)線條造型手法。從十五國到元代,以線造型成為中國畫的基本特點(diǎn)。[2]敦煌壁畫運(yùn)用生動且隨意的線條描繪,流露出本質(zhì)之美,永恒之美。我國的傳統(tǒng)動畫也運(yùn)用線描手法進(jìn)行動畫形象塑造。在動畫的發(fā)展過程中,老一輩藝術(shù)家將動畫線條的特征基本概括為準(zhǔn)、挺、勻、活。[3]
莫高窟的唐代飛天壁畫,整體運(yùn)用淡墨色來勾畫人物的形象,部分人物的面部則用朱紅色進(jìn)行二次勾勒上色。在描繪飛天的重要部位時(shí),運(yùn)筆則較輕徐、緩慢。飛天各異的動勢情態(tài),運(yùn)用抑揚(yáng)頓挫的線條描繪,給人以暢快淋漓、身臨其境的審美體驗(yàn),如圖1。
(三)空間透視關(guān)系。敦煌壁畫的透視建立在動點(diǎn)、散點(diǎn)透視的基礎(chǔ)上,觀者通過眼睛觀察不同位置環(huán)境情節(jié)下既獨(dú)立又相互聯(lián)系的畫面。[4]其善于表現(xiàn)無限的范圍,空間結(jié)構(gòu)自由多變。在動畫《九色鹿》中,對于空間的表現(xiàn)同樣是缺乏透視的,如山脈的前后空間關(guān)系常給人處在同一空間維度的感覺。動畫中加入少量的虛實(shí)手法,如遠(yuǎn)處山脈的虛化處理和空間的霧化效果,讓人感到山脈在空間位置上漸遠(yuǎn)。
(四)色彩繪制風(fēng)格。敦煌壁畫發(fā)端于佛教的傳入,其目的在于宣揚(yáng)政教服務(wù),故用色習(xí)慣上充分融入佛教色彩,頗具中國繪畫特色,使得彩繪藝術(shù)成為敦煌藝術(shù)的主要成就。如動畫《九色鹿》,開端沙漠中的點(diǎn)點(diǎn)綠洲;隨之而來的烏云密布;冬季的森林籠罩在茫茫白雪,同時(shí),短片中多處運(yùn)用了大量熟褐色,不僅彰顯當(dāng)時(shí)的社會政治背景,也符合敦煌壁畫的用色特點(diǎn),并且給人營造了久遠(yuǎn)的歷史感。
二、敦煌藝術(shù)在動畫中的傳承
在動畫創(chuàng)作中,如何開發(fā)利用好本民族的燦爛文化,成為當(dāng)代動畫創(chuàng)作者應(yīng)認(rèn)真思考的問題,也是振興我國動畫產(chǎn)業(yè)的一大使命。我國動畫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需要將我們民族的文化和人們的情感融入其中,這樣的動畫作品才稱得上成功。只有汲取民族文化的精髓,才能廣為傳播。敦煌壁畫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時(shí)代特色已經(jīng)為我們創(chuàng)作新的動畫風(fēng)格起到了很好的導(dǎo)向作用。[5]憑借動畫藝術(shù)時(shí)代感、時(shí)尚性的特征來推動敦煌藝術(shù)在當(dāng)代年輕人中的傳承。
參考文獻(xiàn):
[1]陸麗娟.現(xiàn)代裝飾藝術(shù)借鑒敦煌藝術(shù)元素的教學(xué)思考[J].高教論壇,2010,(9):74.
[2]吳榮鑒.敦煌壁畫中的線描[J].敦煌研究,2004,(01):42.
[3]劉海.F代動畫線條對敦煌壁畫線條的繼承與發(fā)展[J].新一代,2012,(7):60-61.
[4]徐輝.論敦煌壁畫的透視[J].佳木斯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06,(3):141-143.
[5]高秀軍.敦煌壁畫形象到動畫形象的轉(zhuǎn)化探析[D].蘭州:蘭州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2:18.
作者簡介:
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內(nèi)涵:法律特性的考察和分析
關(guān)于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特性的介紹見諸眾多文獻(xiàn)。學(xué)者們大多借助“民俗”(民間文學(xué))理論認(rèn)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是由廣大民眾集體口頭創(chuàng)作,能表達(dá)他們的共同心聲,并在廣大民眾中世代流傳的文學(xué)藝術(shù),具有民間性、生活性、傳承性等基本特性鱟。我國著作權(quán)法則從法律角度將“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特性概括為區(qū)域性、集體性、傳承性等。對此,本文以為,無論是從文學(xué)藝術(shù)本身特性抑或法律特性方面,回歸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本源——區(qū)域民族性、民間本真性與集體創(chuàng)作性,是界定和區(qū)別不同種類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成果內(nèi)涵之基本要素。而傳承性則是其受法律保護(hù)的前提。這對分析和考察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而言,也是如此。和南道“三條線路”鮞。伴隨著中西經(jīng)貿(mào)繁榮,西域諸國及中亞的宗教、歌舞由此東傳內(nèi)地;中原的歌舞、漢文典籍也隨絲綢、瓷器從這里傳播世界各地。此時(shí)的敦煌,作為“華戎所交一都會”,已然擔(dān)負(fù)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之樞紐”的重任。可以說,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地緣區(qū)域和文化環(huán)境,使得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從產(chǎn)生時(shí)起,即“具有了鮮明個(gè)性,顯示了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力與創(chuàng)造力。”這種鮮明的個(gè)性,首先表現(xiàn)為敦煌民間藝術(shù)表達(dá)所蘊(yùn)含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體現(xiàn)了本區(qū)域民族文化特征。即使是對敦煌石窟佛教文化藝術(shù)而言,它也是“東傳的佛教在一個(gè)具有成熟傳統(tǒng)的封建文化的地方的特有產(chǎn)物,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受外來宗教刺激下出現(xiàn)的新形態(tài)。”一般而言,形成于某地的民間文化藝術(shù),其本民族范圍內(nèi)認(rèn)同感更強(qiáng)烈。但是在長期的文化流傳過程中,一些反映人們精神追求的共性的東西,也往往會突破地區(qū)、語言的障礙,流傳到另一個(gè)民族地區(qū),為當(dāng)?shù)孛褡褰蛹{和吸收后,以當(dāng)?shù)赜蛎褡濯?dú)具特色的文學(xué)藝術(shù)形式表達(dá)并隨之流傳開來。當(dāng)我們循著這樣的思路考察印度佛教文化藝術(shù)在敦煌的傳播過程時(shí),也發(fā)現(xiàn)存在同樣的軌跡。無疑,佛教文化在敦煌的傳播固有敦煌乃中西貫通之咽喉,最先接觸佛教之先驅(qū)因素;有十六國時(shí)期,社會動蕩,戰(zhàn)爭連綿,民眾尋求佛教“出世避禍”的現(xiàn)實(shí)需求;但更有與我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和道義思想宣揚(yáng)的社會基本人性、道
(一)區(qū)域民族性
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創(chuàng)生源于獨(dú)有的內(nèi)外環(huán)境,離不開多元文化的孕育與滋養(yǎng)。我們只有從這一大前提出發(fā),才能準(zhǔn)確把握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產(chǎn)生的歷史脈搏。敦煌地處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東迎華岳,西達(dá)伊吾,南枕祁連,北通大漠,處于我國古代境內(nèi)外各民族交往的十字要津,扼居中亞、西域,交通華夏中原的關(guān)口。公元111年,漢武帝平定匈奴,“分置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等“河西四郡”鮭。后歷經(jīng)各朝政權(quán),通過遷徙漢人居住,保持漢族戍卒,調(diào)整民族關(guān)系等積極措施,河西在較長時(shí)期內(nèi)保持相對穩(wěn)定,得到了與中原漢民族文化同步發(fā)展的歷史契機(jī)。漢晉文化在此生根和發(fā)展鮚。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歷時(shí)既久,其文化學(xué)術(shù)逐漸具有地域性性質(zhì)。”鮪其間,敦煌作為歷史上羌戎、烏孫、月氏、匈奴、鮮卑、吐谷渾、吐蕃、回鶻、粟特、于闐、黨項(xiàng)、蒙古等少數(shù)民族先后聚居的地區(qū),與漢民族共生共息,共融發(fā)展,形成了農(nóng)業(yè)定居文化與游牧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特征。農(nóng)業(yè)定居文化為中原文化的進(jìn)入與漸居主流地位奠定了基礎(chǔ),而游牧民族文化則為中西文化的互動與融合提供了土壤。這一多民族文化的本質(zhì)特征從根本上決定了敦煌文化開放與守成的雙重性。而從敦煌文化藝術(shù)的外生環(huán)境看,經(jīng)貿(mào)的繁榮,也為中西文化交匯提供了可能。隋時(shí),“煬帝西巡”,遣使節(jié)出使西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mào)易”,形成了連通西域,“總湊敦煌”的北道、中道德、秩序主旨相吻合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人們祈求佛陀保佑國泰民安、風(fēng)調(diào)雨順、四鄰友好、健康長壽,人們崇敬三寶(佛、法、僧),盡心盡力開鑿洞窟,修建廟宇,布施師僧,燃燈浴佛,把佛事活動作為盡忠盡孝的一種重要方式,故佛教的傳入非但未受到世俗政權(quán)、百姓的排斥,反而得以推崇。如《魏書•釋老志》所記:“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于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像教彌增矣。”伴隨著這種融入傳統(tǒng)中原儒教倫理思想的本土佛教文化觀念的逐漸形成和深入民間,宣揚(yáng)世家儒家文化的忠孝觀和中原文化開始出現(xiàn)在壁畫藝術(shù)中。“北魏時(shí)期的敦煌莫高窟洞窟共18個(gè)其壁畫多為佛本生故事和千佛為主要題材。北周時(shí)期的洞窟共10個(gè)其壁畫內(nèi)容則首次出現(xiàn)了講孝子和善兄惡弟的故事。”壁畫中不僅有為“觀佛修行”目的各類佛教畫,還有描繪民族神話傳說的神怪畫。如莫高窟第249窟、285窟中集中了伏羲、女媧、龍、鳳、朱雀、飛仙(羽人)、飛廉、方相氏、東王公、西王母等神話形象,它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形態(tài)。段文杰先生對此評價(jià)道,“這類土生土長的題材經(jīng)常和佛教故事畫在一起,形成了‘中西結(jié)合’、‘土洋結(jié)合’把道家的‘羽化升天’和佛教的‘極樂世界’形成了一體,這正是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逐漸‘民族化’,和道家、儒家思想逐步融合的反映。”她“既不是西來的,也不是東去的,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敦煌這個(gè)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中與外來文化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從物質(zhì)文化史的角度看,由于物質(zhì)文化的創(chuàng)造是人類的一種精神活動過程,因此,人類的精神文化,如風(fēng)俗、習(xí)慣、禁忌、道德、宗教以及政治制度等,其本身雖不屬于物質(zhì)文化的范圍,但它對物質(zhì)文化的價(jià)值取向,卻會發(fā)生十分強(qiáng)烈的影響。它可以決定物質(zhì)文化的具體發(fā)展方向,甚至對其發(fā)展起推動或阻礙作用。故此,史葦湘先生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和文化“不僅是敦煌文化藝術(shù)的基礎(chǔ),而且是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其內(nèi)容與形式以及對內(nèi)地和西來的各種藝術(shù)風(fēng)格選擇取舍的主要決斷力量。”與此同時(shí),敦煌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之樞紐”,在堅(jiān)守自己傳統(tǒng)文化、本土文化的同時(shí),還展示了其文化開放和包容精神,表現(xiàn)出了多種文化交融的獨(dú)有文化藝術(shù)魅力。以敦煌石窟藝術(shù)為例。石窟寺的建造源于天竺,但敦煌石窟的建造卻是在崖面鑿窟的同時(shí)結(jié)合了我國傳統(tǒng)木構(gòu)建筑的特點(diǎn)。不但石窟內(nèi)部,而且其外面同樣有用木頭修出來的窟檐、柱子等,“等于是造一個(gè)房子把這個(gè)石窟蓋在里面”。至于后來敦煌石窟發(fā)展出的“殿堂式的石窟,有點(diǎn)像我們現(xiàn)在的佛教寺廟了”。石窟壁畫中的飛天形象則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又一杰作。“飛天故鄉(xiāng)雖在印度,但敦煌飛天卻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國道教羽人、西域飛天和中原飛天長期交流、融合為一的結(jié)果。”可見,敦煌文化藝術(shù)是在長期多元文化交流中,汲取中西、各民族文化藝術(shù)的有益成分,創(chuàng)生出的一種更具本地域民族文化色彩的獨(dú)有的民間文化藝術(shù)。
(二)民間本真性
敦煌民間篤信佛教,但更注重“用重于信”。當(dāng)敦煌民眾通過藝術(shù)手段塑造一個(gè)個(gè)佛陀、描繪一幅幅“凈土世界”時(shí),他們把對世俗生活的熱情和美好向往融入了對“佛國世界”的理解和想象,使得敦煌民間藝術(shù)表達(dá)為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率性需要而創(chuàng)造,凸顯了其民間藝術(shù)的“本真性”。例如,敦煌石窟壁畫藝術(shù)中,小孩“聚沙成塔”皆可成佛(而不是“累世苦修”)的《法華經(jīng)變》;環(huán)繞在彌勒佛周圍的“一種七收”、“樹上生衣”、“路不拾遺”、“女子五百歲出嫁”、“送八萬四千歲的老人入墓”的《彌勒上生下生經(jīng)變》;一心念佛,“九品往生極樂世界”的《阿彌陀經(jīng)變》;只要念一聲“藥師佛”的名號,一切無救、無歸、無醫(yī)、無親、無家等待苦難皆可得救,逢兇化吉,遇難呈祥的《藥師變》等等。這些表達(dá)當(dāng)?shù)仄胀癖娦扌蟹鸱ǖ拿篮孟蛲惆l(fā)他們的心聲的藝術(shù)早已超越了單純的佛教的信仰,而成為了“一種獨(dú)立的審美對象。”為使這樣的藝術(shù)表達(dá)更真實(shí)、更親切,他們甚至將世俗勞動生活的場景,也“搬到”壁畫中。如,人們在壁畫世界中描繪的“彌勒凈土世界”同現(xiàn)實(shí)世界一樣,要耕地、播種、收獲、收割、打谷、揚(yáng)場,要向地主和官府交租(第445窟);有行走在千里迢迢的絲綢之路之上的風(fēng)塵仆仆的商旅(第296、302窟頂、420窟)與泛海商途中陷入困境行劫的風(fēng)險(xiǎn)(第45窟南壁);有兒童在學(xué)校讀書(第231窟)、牧羊女在圈棚邊擠奶(第159、9、61等窟)、官府在拷打百姓(第159窟)、男女談情說愛(第85窟)與嫁娶婚禮(第12、85窟)等。這些形形的“眾生實(shí)相”,“早已超越了,真正成為了充滿無窮活力,透著濃濃生活氣息的民間藝術(shù)。”
(三)集體創(chuàng)作性
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具有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還表現(xiàn)在,它并非某個(gè)個(gè)體的創(chuàng)作行為,而是群體智慧的結(jié)晶。從歷史看,世居敦煌的人口中有本地少數(shù)民族、中原移民,也有西域各民族,在這樣一個(gè)民族大融合的環(huán)境中,各民族基于對共同、風(fēng)俗習(xí)慣、價(jià)值追求的認(rèn)同和精神生活需要,集體創(chuàng)造著適應(yīng)本地域多民族共同精神生活需要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以敦煌石窟藝術(shù)表達(dá)的創(chuàng)造為例,雖然體現(xiàn)了捐窟人個(gè)人目的和需要,但真正鑿窟、繪壁與造像的無疑是具有高超技藝的民間畫(塑)師、心存虔念而又以畫(塑)技藝謀生的窮苦匠人、有一定打窟經(jīng)驗(yàn)的下層工人等構(gòu)成的龐大的創(chuàng)作群體。這在敦煌遺書中有大量記載:“選上勝之幽巖,募良工而鐫鑿。”(P.3405《營窟稿》)“更鑿仙巖,鐫龕一所,召良工而樸琢,憑巧匠以崇成。”(P.4638)“乃召巧匠、選工師,窮天下之譎詭,盡人間之麗飾。”(P.2551)“匠來奇妙,筆寫具三十二相無虧;工召幽仙,彩妝而八十種好圓滿。”(P.3556《康賢照贊》)。對這些民間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者的行為,史葦湘先生充滿激情地予以了評價(jià)和肯定,“誰是莫高窟藝術(shù)真正的創(chuàng)造者?廣義地講,是公元4世紀(jì)到14世紀(jì)敦煌地方普通的農(nóng)牧民、手工工人、下層士兵和各族勞動者。他們是敦煌佛教的基本信眾。莫高窟的建造,他們不但是物質(zhì)條件的提供者,是鑿窟勞役的承擔(dān)者,更重要的是那些工匠,他們是敦煌壁畫、彩塑藝術(shù)美的直接創(chuàng)造者。”當(dāng)然,強(qiáng)調(diào)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集體創(chuàng)造性,并非一概否定民間專業(yè)藝人的存在。事實(shí)上,在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長期創(chuàng)造和傳播中,特定范圍的世家或師徒相傳往往是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不斷被創(chuàng)造的一種重要方式。他們往往是一批職業(yè)化或半職業(yè)化的民間藝人隊(duì)伍。敦煌壁畫的畫師中,也有一些職業(yè)畫師存在。如瓜沙歸以軍節(jié)度使軍府里設(shè)有畫院、上置都勾當(dāng)畫院師、下置知畫行都料、都畫匠、都塑匠等。此外,還有當(dāng)?shù)厮略寒嫾液蛠碜晕饔蚧蛑性漠嫀煹取!豆?jié)度押衙董保德建造蘭若功德頌》就有對敦煌畫師董保德的技藝的記載:“手跡及于僧繇,筆勢鄰于曹氏。畫蠅如活,佛鋪妙越于前賢;邈影如生,圣會雅超于后哲。而又經(jīng)文粗曉,禮樂兼精,實(shí)佐代之良工,乃明時(shí)之膺世。”可以說,正是這些民間專業(yè)藝人的加入,使敦煌石窟藝術(shù)有了更為生動和豐富的表現(xiàn),成就了敦煌民間藝術(shù)表達(dá)的輝煌。綜上,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是由敦煌這一特定文化區(qū)域內(nèi)的多民族,在堅(jiān)守我國傳統(tǒng)、本土文化藝術(shù)的基礎(chǔ)上,吸收融合外來文化藝術(shù),集體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文學(xué)藝術(shù)成果。區(qū)域民族性系其第一特性;民間本真性系其第二特性;集體創(chuàng)作性系其第三特性。
敦煌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外延:多元化類型與多維度表現(xiàn)樣態(tài)
敦煌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十分豐富,不僅有民間口頭、語言表達(dá);民間音樂、舞蹈;民間、神怪故事與傳說;民間服飾藝術(shù)表達(dá);還有民間壁畫、雕塑、建筑技藝;木刻版畫、葫蘆雕刻、壁畫剪紙技藝;石窟壁畫、雕塑、建筑美術(shù)圖像藝術(shù)表達(dá)等等,體現(xiàn)了成果類型的多元化。在表現(xiàn)方式(載體)上,既有通過口頭、肢體語言表現(xiàn),還有平面、立體三維表現(xiàn),特別是敦煌壁畫、雕塑、建筑圖像美術(shù)藝術(shù),這種實(shí)物表達(dá)形式既是這類民間藝術(shù)的客體呈現(xiàn),又是承載表達(dá)內(nèi)容的有形物質(zhì)載體,二者緊密結(jié)合,共同構(gòu)成了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多維度表現(xiàn)樣態(tài)。為清晰表述上述內(nèi)容,本文以敦煌民間文藝表達(dá)的成果客體的多元化為中心,區(qū)分非石窟和石窟兩類表現(xiàn)載體,將敦煌民間文藝表達(dá)的成果類型分為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與類非作品表達(dá)兩種。圖例歸納與說明如下:
(一)敦煌口頭說唱文學(xué)、語言表達(dá)
典型的敦煌民間口頭文學(xué)有:敦煌曲子詞、敦煌變文等講唱文學(xué)。例如,河西寶卷即是至今流傳于甘肅省河西走廊一帶的民間講唱文學(xué)的代表。它是在唐代敦煌變文、俗講以及宋代說經(jīng)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成的一種民間吟唱文學(xué)。河西寶卷盛行于明、清至民國時(shí)期,主要有佛教類、歷史故事類、神話傳說類、寓言類四種類型。內(nèi)容的主題多譴責(zé)忤逆兇殘,宣揚(yáng)孝道和善行。裕固族語言則是口頭流傳的民族民間語言的又一典型。裕固族是一個(gè)歷史悠久、甘肅獨(dú)有的少數(shù)民族,由于其文字失傳,口頭語言不僅是裕固人民相互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是其文學(xué)傳承的主要方式。一般來講,一個(gè)民族只有一種屬于本民族的語言,而裕固族卻有著兩種屬于本民族的語言,即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語言和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語言,這種情況在我國少數(shù)民族中較為少見。裕固族的兩種語言中保留了許多古突厥語特點(diǎn),是回鶻語言的“嫡語”,與古代維語最接近,是流傳至今的活的語言,對研究我國古代西部民族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價(jià)值。
(二)敦煌民間音樂、舞蹈
敦煌民間音樂、舞蹈是敦煌樂舞體系的重要組成內(nèi)容之一。敦煌樂舞體系主要由敦煌遺書中的樂舞文獻(xiàn)史料和敦煌石窟中的壁畫樂舞圖像,以及敦煌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樂舞文化藝術(shù)三部分所組成,三者共同構(gòu)成繁盛的敦煌樂舞氣象。其中,敦煌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樂舞藝術(shù)是敦煌樂舞文獻(xiàn)史料記載、敦煌壁畫樂舞圖像表達(dá)的基礎(chǔ),敦煌壁畫樂舞圖像表達(dá)雖有一定的藝術(shù)加工和夸張表現(xiàn)成分,但總體未脫離那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生活,是敦煌民間音舞藝術(shù)的生動描繪。例如,酒宴著辭作為敦煌民間比較文雅的一種宴飲方式,在敦煌文獻(xiàn)中有大量記載;宴飲歌舞場面在唐五代壁畫內(nèi)容中也有生動反映,如,莫高窟五代第61窟的宴飲圖中,包括維摩詰在內(nèi)的7人坐在食床兩旁,食床上放有裝酒的器皿和其他餐飲具。其中兩人在奏樂,一人在翩翩起舞。以羅庸、葉玉華、王克芬、柴劍虹為代表的學(xué)者在對藏經(jīng)洞所出“敦煌舞譜”殘卷進(jìn)行分析后指出,這些舞譜殘卷所記錄的舞蹈系漢、魏“屬舞”和唐人酒宴上的“打令舞”,說明民間筵宴舞蹈很早就在敦煌地區(qū)流行。如今在西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酒筵游戲場合,為歡歌助興,營造熱烈氣氛,酒宴著辭、敬茶、獻(xiàn)酒邀舞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娛樂節(jié)目,也是地方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敦煌節(jié)日音樂風(fēng)俗中,還保留了古代西涼樂舞的遺風(fēng),如古代軍旅出征樂舞的遺存——“涼州四壩滾鼓子”(民間鼓樂舞蹈)以“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氣勢,如今仍活躍在涼州北鄉(xiāng)一帶。此外,還有婚慶樂舞、春節(jié)社火(如涼州的民間社火);大量的勞動和生活歌謠,如放羊歌、奶牛犢歌、割草歌、搟氈歌、哭嫁歌等。
(三)敦煌民間宗教、神怪故事、傳說
在敦煌佛教文化題材中,有許多為民間百姓所熟知的宗教或神話故事。即便是宗教故事也都加入了本地信眾的理解。例如,《敦煌變文》中記載有《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講述目連救母的故事;《舜子變》講述舜子至孝的故事;《董永變文》講述董永遇仙女的神話傳說故事等。那一幅幅精美的敦煌壁畫更是講述著一個(gè)個(gè)神奇動人的故事傳說。如為民間百姓所熟知的水月觀音經(jīng)變、千手千缽文殊經(jīng)變、千手千眼觀音經(jīng)變、報(bào)父母恩重經(jīng)變等;描繪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普行六度的種種事跡與善行故事,如尸毗王割肉貿(mào)鴿;九色鹿拯救溺人;薩埵那太子舍身飼虎;睒子孝養(yǎng)盲親等。同時(shí),我國傳統(tǒng)神話中的西王母與東王公、伏羲與女媧、涼州民間司農(nóng)之神天公與天母的故事;創(chuàng)世神話、善惡神話;遠(yuǎn)古歷史傳說、地方風(fēng)俗傳說、風(fēng)物傳說等也在敦煌民間流行。
(四)敦煌民間服飾藝術(shù)表達(dá)
服飾是一個(gè)民族或民族群體歷史文化積淀的產(chǎn)物,郭沫若曾說,“由服飾可以考見民族文化發(fā)展的軌跡和兄弟民族間的相互影響,歷代生產(chǎn)方式、階級關(guān)系、風(fēng)俗習(xí)慣、文物制度等。”敦煌作為多民族匯聚地,各民族服飾文化多姿多樣,例如,裕固族婦女的頭面和紅纓帽、保安族男子服裝的腰刀配飾、不同地區(qū)的藏族服飾等。這些民族服飾反映了本地域少數(shù)民族文化歷史傳承、人生禮儀、和生活習(xí)俗。它們以美觀大方、色調(diào)和諧、格調(diào)獨(dú)特的敦煌民間服飾共有特征,反映了該地域民族獨(dú)有的審美觀念和豐富的文化藝術(shù)內(nèi)容。
(五)敦煌民間壁畫、雕塑、建筑技藝,木刻版畫、葫蘆雕刻技藝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個(gè),有歷代壁畫五萬多平方米,是我國也是世界上壁畫最多的石窟群。石窟藝術(shù)源于印度,但印度傳統(tǒng)的石窟造像以石雕為主,敦煌莫高窟因巖石堅(jiān)硬、砂石疏松,故以泥塑造像為主。除南北大像為石胎泥塑外,其余多為木架結(jié)構(gòu)的彩塑尊像。敦煌彩塑藝術(shù)的制作方法可分為圓塑、浮塑、影塑和懸塑四種。無論何種塑形,第一步都是制作出塑像的大體輪廓。輪廓完成后,接下來的程序是用泥。用細(xì)泥塑出人物的表層細(xì)部,諸如衣褶、佩飾、五官等;再下來便是剔除、增補(bǔ)和修改,主要是對一些細(xì)部如臉部、頭部、衣紋等的刻劃;最后是敷彩。千姿百態(tài)的塑像顯示了敦煌“塑匠”們嫻熟的技藝、就地取材(如用當(dāng)?shù)刂饕吧参镘杠覆菟艹鲂误w,用細(xì)泥塑出人物表層細(xì)部)的超人智慧和豐富的想象力。石窟壁畫的繪畫技藝中則基本保留了我國傳統(tǒng)的壁畫藝術(shù)制作步驟,如一朽(行話叫做“攤活,即用炭條打稿”)、二落(行話叫“落墨”,即勾線)、三成(行話叫“成管活”,即著色與完成)。同時(shí)對一些壁畫還進(jìn)行了特殊處理,——“瀝粉貼金”,如菩薩、飛天的花冠、瓔珞、法器等,以增強(qiáng)畫面的立體造型感和豐富的視覺效果等。在“白描稿本”和相對約定俗成的“畫訣”使用方面;在金色制造法、立粉法、涂色法和暈染法等民間技法方面,也都運(yùn)用了民間傳統(tǒng)技法。在繪畫顏料的制作和調(diào)配上,更有獨(dú)到的選料和工藝,敦煌壁畫顏料主要來自進(jìn)口寶石、天然礦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選用這種用礦物顏料繪制的壁畫能夠歷經(jīng)千年而不褪色。隨著敦煌旅游業(yè)迅速發(fā)展,近十年來以敦煌佛教藝術(shù)為題材的木刻版畫、葫蘆雕刻、壁畫剪紙等手工藝品產(chǎn)業(yè)也得到較大的發(fā)展。如今,超過500名民間藝人進(jìn)行當(dāng)?shù)厥止に嚻返膭?chuàng)作與銷售,民間藝術(shù)產(chǎn)業(yè)已成為敦煌旅游的新名片。
(六)敦煌石窟壁畫、雕塑、建筑美術(shù)藝術(shù)表達(dá)
本文關(guān)于“美術(shù)藝術(shù)”的稱謂,是專指以平面或立體方式呈現(xiàn)的敦煌石窟壁畫、雕塑、建筑圖像藝術(shù)。它們不同于其反映的主題藝術(shù)內(nèi)容——樂舞藝術(shù)。同時(shí),也要與前述的敦煌壁畫、雕塑、建筑技藝區(qū)別開來。技藝是呈現(xiàn)敦煌美術(shù)圖像藝術(shù)的手段,美術(shù)圖像藝術(shù)則是技藝展現(xiàn)的結(jié)果。敦煌壁畫現(xiàn)存約5萬平方米,最大畫幅40余平方米。時(shí)代從十六國到元代,千年不衰。莫高窟壁畫內(nèi)容豐富,堪稱“墻壁上的美術(shù)館”。分為佛教畫、我國傳統(tǒng)神話畫及裝飾圖案畫、社會風(fēng)俗畫三大類。其中,佛教畫中有包括各種佛像及菩薩,如三世佛、七世佛、釋迦、多寶佛、賢劫千佛、文殊、普賢、觀音、勢至,還有天龍八部等說法圖933幅、佛像12,208身;有水月觀音經(jīng)變、如意輪觀音經(jīng)變、千手千缽文殊經(jīng)變、千手千眼觀音經(jīng)變、福田經(jīng)變千余壁;有繪述釋迦牟尼佛過去若干世為菩薩時(shí)忍辱犧牲、教化眾生、普行六度的種種事跡與善行的本生故事畫;有講述釋迦牟尼成佛后度化眾生的因緣故事畫和描述釋迦牟尼佛從入胎、出生、成長、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槃等被神化了的佛傳故事畫;還有佛教史跡故事畫。第二類中國傳統(tǒng)神話畫,主要有第249窟、第285窟表現(xiàn)東王公、西王母駕龍車、鳳車出行;伏羲、女媧;白虎、朱雀和“雷公”、“雨師”等眾神的壁畫。莫高窟壁畫中的裝飾圖案畫主要是平棋和藻井,屬于建筑頂部的裝飾。社會風(fēng)俗畫中有供養(yǎng)人畫像、出行圖、山水畫等。這些壁畫多數(shù)是依據(jù)佛經(jīng)繪制的佛教宣傳畫,但在造型藝術(shù)表現(xiàn)時(shí),古代藝術(shù)匠師們卻是根據(jù)當(dāng)時(shí)社會生活現(xiàn)實(shí)塑造神靈和人物形象、生活場景,因而它直接、間接地反映著社會歷史、民間生活。敦煌石窟彩塑,是“東方雕塑”的又一大杰作。它是在泥塑外層干后敷彩施色,故稱彩塑。莫高窟彩塑保存著自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等10個(gè)朝代的彩塑(包括影塑)3000余身,其中圓雕2000多身,浮塑1000余身。除此外,敦煌石窟彩塑還包括榆林窟、東西千佛洞彩塑。敦煌彩塑的對象有:身披袈裟,頭有肉髻,耳長及肩,眉間有白毫,指間有蹼,腳掌有,手印隨說法、降魔、苦修、禪定的佛像;頭戴花冠,身著天衣,腰系長裙,肩披長巾飄帶,袒上身,胸前掛瓔珞,腕飾釧鐲,面容端莊文靜,肌體豐滿圓潤,以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菩薩像;以大弟子迦葉(老者形象)和小弟子阿難(少年姿態(tài))為代表的弟子像;威武神氣的天王、金剛力士像等。莫高窟的石窟建筑藝術(shù)。莫高窟的石窟唐時(shí)有建筑千余洞,現(xiàn)存石窟492洞,其中魏窟32洞,隋窟110洞,唐窟247洞,五代窟36洞,宋窟45洞,元窟8洞。其石窟建筑藝術(shù)主要指其形制及其造型。敦煌石窟中,最能體現(xiàn)其地域民族特色的石窟形制及其造型有中心塔柱窟,又稱塔廟窟,是指建在洞內(nèi)的寺院。它的出現(xiàn)除受印度、新疆造窟形式(宗教禮儀中繞塔禮拜的習(xí)俗)影響外,還與漢地寺院以塔為標(biāo)志的習(xí)俗有密切關(guān)系,是石窟藝術(shù)逐漸漢化的產(chǎn)物。另外,覆斗頂形窟也很像我國傳統(tǒng)房屋布局中的布“帳”。這種形制在印度以及新疆地區(qū)很少見到,一般認(rèn)為也是受漢地墓葬形式影響而致的本地產(chǎn)物。此外,還有殿堂窟、大像窟。莫高窟初唐第96窟(即北大像窟,又稱九層樓,彌勒佛像高33米)是依山崖而坐,內(nèi)為石胎,外面敷泥賦彩而建。大像窟的建筑形式是我國傳統(tǒng)木結(jié)構(gòu)的殿堂建筑與印度石窟建筑結(jié)合的典型產(chǎn)物。由于佛像通體的高大和窟檐外觀的氣派,大像窟成為了敦煌石窟建筑的中心和象征。
總之,在敦煌石窟圖像藝術(shù)當(dāng)中,雕塑是石窟的主體,壁畫因塑像而成,建筑則為雕塑和壁畫的繪制提供了框架支撐。三者結(jié)合,相互輝映,層次分明,共同構(gòu)成了獨(dú)具敦煌地域與民族特色的石窟立體藝術(shù)。上述多元化的敦煌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成果或者以作品形態(tài)存在,如那些獨(dú)立地表達(dá)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或者以非作品形態(tài)(如符號、素材、裝飾圖案、技藝表達(dá)等)存在。這里,本文未采用著作權(quán)法的一般分類標(biāo)準(zhǔn),是因著作權(quán)法只有對作品的分類,而無非作品的類型概括,如果沿用一般作品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則無法涵括體現(xiàn)敦煌民族民間藝術(shù)特征的多元化類型。例如,那些為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而存在的民間技藝,甚至不屬于文學(xué)藝術(shù)范疇,但卻實(shí)實(shí)在在地被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表達(dá)聯(lián)系在一起,甚至就是其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要求和必經(jīng)的步驟、藝術(shù)表達(dá)形式本身。即便不能用作品的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這類技藝成果,也仍應(yīng)歸屬敦煌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成果之列,因?yàn)閺膰H上對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范圍劃定看,民間技藝即涵括在其中。
敦煌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傳承:動態(tài)化承繼與多樣式表現(xiàn)
由于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創(chuàng)生至今已逾千年,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是否傳承,以何種方式傳承,不僅法律角度探討闕如,對敦煌學(xué)界的相關(guān)研究也有待認(rèn)真分析。有學(xué)者認(rèn)為,敦煌石窟藝術(shù)“始于4世紀(jì),而終結(jié)于14世紀(jì)”(顏廷亮)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敦煌藝術(shù)的下限既不是元代,也不是民國時(shí)期,而應(yīng)是清末”(易存國)。這些觀點(diǎn)對敦煌石窟藝術(shù)在元代走向衰弱。清末鑿窟行為停止的歷史做了闡述,但對之后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是否傳承,實(shí)際并未言及。對此,本文的理解是,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斷不能以偏概全,以“石窟鑿窟行為的停止”來否認(rèn)敦煌民間藝術(shù)的客觀存在和傳承,因?yàn)槎卟痪哂幸灰粚?yīng)的關(guān)系和必然的聯(lián)系。如前所述,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不僅僅指敦煌“非石窟文化藝術(shù)”。還應(yīng)當(dāng)包括敦煌地區(qū)民族創(chuàng)造的諸多流傳在民間的“非石窟文化藝術(shù)”,如,敦煌民間筵宴舞蹈、涼州鼓舞等至今還在民間延續(xù)和傳承。僅以“敦煌石窟鑿窟行為的停止”為例證,來說明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止步”,不具種概念對屬概念外延的周延性。進(jìn)一步而言,“敦煌石窟鑿窟行為的停止”是否意味著其敦煌石窟民間藝術(shù)表達(dá)的“止步”,也是值得商榷的。有學(xué)者認(rèn)為“自1900年敦煌藏金洞發(fā)現(xiàn)以來,敦煌就進(jìn)入了學(xué)術(shù)層面的新時(shí)期,雖然略有重修、重繪、更多是出于維修而非主動的創(chuàng)作。故此,敦煌石窟藝術(shù)的下限只能定于清朝末年。”(易存國)這實(shí)際又為敦煌石窟藝術(shù)表達(dá)的延續(xù)劃定了第二條標(biāo)準(zhǔn),即一定是原樣態(tài)的創(chuàng)作。對此理由,本文也不敢茍同。這里首先涉及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傳承的一個(gè)基本問題需要厘清,是“藝術(shù)表達(dá)本身的傳承”或是“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原樣式)的傳承”?本文以為兩者有實(shí)質(zhì)的不同。從歷史視角看,“隨著自然和社會生活的發(fā)展變化,文化藝術(shù)表達(dá)本身和傳承形式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均會有所不同,呈現(xiàn)動態(tài)變化。”多樣式表現(xiàn)正是其動態(tài)變化的必然反映和客觀要求。我們無法要求某類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固守原有的表現(xiàn)形式或傳承樣式,否則會遏制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生長。為此,固定于某種外在表現(xiàn)方式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傳承不是我們的追求。我們看待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傳承,是看它的民間創(chuàng)作源頭及仍在民間不斷延續(xù)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表達(dá),追求的是無論采取哪種傳承方式再現(xiàn)的民間藝術(shù)表達(dá),只要保有本地域民族民間藝術(shù)屬性和其藝術(shù)表達(dá)的基本特征,反映了本地域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習(xí)俗,都應(yīng)當(dāng)將它們視為一脈相承的文學(xué)藝術(shù),即貫徹了“藝術(shù)表達(dá)本身的傳承”。我們不妨將此歸結(jié)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動態(tài)傳承性”。而這種隨時(shí)代而變的動態(tài)傳承性,反過來又證明了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被不斷創(chuàng)造的屬性。實(shí)踐證明,愈是能夠動態(tài)傳承的事物,愈印證著其長久的生命力。這對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而言亦然。如前所述,敦煌民間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豐富,表達(dá)成果類型多元化。在延續(xù)千年的歷史中,因不同時(shí)期社會、生活、經(jīng)濟(jì)背景不同,其藝術(shù)風(fēng)格和形式、手法千變?nèi)f化。我們不能因?yàn)樗鼈儾皇浅鲇谕凰囆g(shù)表現(xiàn)形式,而否認(rèn)這種藝術(shù)的同質(zhì)表達(dá)。例如,對那些壁畫藝術(shù)而言,“屬于何種教派,采用何種經(jīng)典,參照何種論疏,請哪一派畫師,作何種形式的構(gòu)圖,使用何種筆墨,形成何種色調(diào),都不是單純的或單純的藝術(shù)技巧問題,而應(yīng)該看到這些藝術(shù)背后有著共同審美觀念、生活習(xí)俗、歷史傳統(tǒng)等。”可見,我們在判斷是否是某類型敦煌民族民間藝術(shù)表達(dá)的傳承時(shí),注重的是這種藝術(shù)表達(dá)的同質(zhì)性,而非傳承方式的唯一性。以此觀照敦煌石窟藝術(shù)的傳承。敦煌壁畫在元代或清末之前,歷代曾在原壁畫基礎(chǔ)上進(jìn)行過延續(xù)創(chuàng)作,甚至是利用原敷面進(jìn)行再繪制,有的洞窟被后代多次重修和維護(hù),使其保有了原實(shí)物表現(xiàn)形式的再現(xiàn)和技藝的再延續(xù)。雖然因歷史和社會變遷,清末造窟停止,繼續(xù)在敦煌鳴沙山崖壁上開鑿石窟、繪制壁畫、進(jìn)行雕塑等已客觀不能且遭法律禁止,但敦煌石窟美術(shù)藝術(shù)的傳承并未完全走向“終止”。從民國至今,對敦煌石窟的修繕、維護(hù),就涉及到了對壁畫、雕塑的重修、重繪活動。不管是出于藝術(shù)研究或維護(hù)的何種目的,基于客觀條件限制,以敦煌學(xué)家張大千、段文杰先生為代表的諸多學(xué)者對石窟壁畫的“仿真臨摹”,在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看來,就是一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至于將這種創(chuàng)造看作是對民間藝術(shù)表達(dá)的傳承創(chuàng)造或是演繹創(chuàng)作,都無損其“創(chuàng)作”的性質(zhì)。由于它們與敦煌傳統(tǒng)壁畫表達(dá)藝術(shù)“一脈相承”,因此,就是對敦煌壁畫美術(shù)藝術(shù)表達(dá)的“活態(tài)傳承”。再從石窟藝術(shù)表達(dá)的基礎(chǔ)——技藝的傳承看,敦煌壁畫中運(yùn)用的“白描稿本”和相對約定俗成的“畫訣”、金色制造法、立粉法、涂色法和暈染法等民間技法,仍在民間運(yùn)用;泥塑藝術(shù)(技藝)作為我國古老的民間藝術(shù),從陶器塑到佛像塑,從古至今也未絕跡。敦煌文物研究近年來對敦煌壁畫、雕塑的修復(fù),即運(yùn)用了這些古法,做到了“逼真”。一些民間手工創(chuàng)作的“敦煌飛天”、“反彈琵琶”壁畫、雕塑藝術(shù)品,也沿襲了這些相同或相似的藝術(shù)表達(dá)手法和技藝。可以說,它們與石窟壁畫、雕塑藝術(shù)表達(dá)系“一脈相承”,是對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包括傳統(tǒng)技藝)的動態(tài)傳承。當(dāng)我們運(yùn)用“動態(tài)傳承”的標(biāo)準(zhǔn),進(jìn)一步將敦煌民族民間藝術(shù)表達(dá)置于千余年的歷史長河中,做一番宏觀考察時(shí),我們發(fā)現(xiàn),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非但未因歲月沖刷完全消亡,相反,卻呈現(xiàn)出另一番旺盛景象。這些悠久而古老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一部分至今仍以口授、身傳表達(dá)方式,流傳在民間。例如,涼州獅舞就是長期流傳在武威(古稱涼州)地區(qū),一種古老的民間舞獅藝術(shù)的典型代表。唐代詩人白居易曾經(jīng)在《西涼伎》中對這種“長嘯”長安城的“獅子舞”有過精彩描寫,“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如今成為了河西涼州地區(qū)群眾慶祝節(jié)日喜慶的必備活動。而另外一部分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則既通過書面文本、建筑、雕塑、壁畫等實(shí)物形式得以記載和保存,如在敦煌壁畫、雕塑、建筑藝術(shù)表達(dá)中呈現(xiàn)(或是其表達(dá)技藝)或被敦煌遺室文獻(xiàn)資料所記載,同時(shí),也通過實(shí)踐活動、技藝延續(xù)、不斷創(chuàng)新傳承表現(xiàn)方式,動態(tài)流傳在民間。例如,敦煌樂舞,被視為敦煌藝術(shù)的永恒“標(biāo)志”,成就了敦煌藝術(shù)的輝煌。如前文所述,自漢、魏時(shí)就敦煌樂舞已流行于民間和宮廷,至今在河西走廊各地等地仍能見到留有敦煌舞遺風(fēng)和特色的民間舞蹈,如“涼州舞獅”,“酒宴著詞樂舞”、“打令舞”等。它們不僅在敦煌那五余萬平方米的石窟壁畫被塑造,在敦煌遺書“敦煌樂譜”和“敦煌舞譜”中殘卷被記載,而且敦煌樂舞的藝術(shù)表達(dá)傳承如同敦煌樂舞藝術(shù)蘊(yùn)含的“開放、時(shí)尚”精神,在逾千年歷史的長期演變中,還不斷創(chuàng)新。現(xiàn)今,根據(jù)敦煌樂舞壁畫以及敦煌舞譜、樂譜資料整理,由我國音樂舞蹈家“復(fù)原”的“敦煌舞”成為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舞種的新流派,敦煌古樂也“翩然流眄于今日之舞臺。”以《絲路花雨》、《大夢敦煌》、《千手觀音》、《敦煌韻》等為代表,根據(jù)敦煌舞樂改變的一批現(xiàn)代敦煌舞劇的面世,更使流傳千年的《霓裳羽衣舞》、《西涼樂舞》、《唐韻胡旋》、《水月觀音》、《妙音反彈》、《千手觀音》等敦煌樂舞形象表達(dá)廣泛展示在世人面前。其中,那“妙音反彈”伎樂天(反彈琴瑟形象)、飄逸神往的飛天,至今仍綻放著無與倫比藝術(shù)魅力,扎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藝術(shù)中,成為了本區(qū)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這些鮮活的實(shí)例驗(yàn)證著,在兩千年的歷史傳承中,敦煌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非但未因歲月沖刷完全消亡,而是以其獨(dú)有的方式頑強(qiáng)生長在民間,即以不斷創(chuàng)新的表現(xiàn)方式和多元化的活態(tài)傳承,延續(xù)著其延綿不斷的旺盛生命力。
關(guān)鍵詞:敦煌;壁畫;飛動之美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4)15-0023-01
敦煌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人類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敦煌壁畫在其文化中占據(jù)主要地位,其藝術(shù)博大精深,自成體系。它與石窟建筑藝術(shù)、雕塑藝術(shù)共同構(gòu)成敦煌藝術(shù)的整體面貌,為后世留下了一筆豐厚的藝術(shù)遺產(chǎn)。敦煌壁畫汲取東西方的影響,題材十分廣泛,涉及人物、山水、建筑等。容量巨大,色彩豐富,創(chuàng)造了獨(dú)特的形象,給人以“天衣飛揚(yáng),滿壁風(fēng)動”的“飛動之美”。本文就是從“飛動之美”在敦煌壁畫藝術(shù)中產(chǎn)生的原因、體現(xiàn)及其內(nèi)在的思想底蘊(yùn)三個(gè)方面加以論述來展示人類文化中的這朵奇葩。
一、“飛動之美”的文化產(chǎn)生
中國人民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總其大要即“天人同一觀”,認(rèn)為人和萬物同出于大自然――原始圖騰就反映了這種觀念。正是這種觀念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面貌和藝術(shù)結(jié)構(gòu)的基本特征。
敦煌壁畫的“飛動之美”通過藝術(shù)家自己的藝術(shù)修養(yǎng),“通過‘三波九折’、‘三停九象’,點(diǎn)、線、面的曲直剛?cè)帷⒐催B并置、收放疏密、空間分割、賓從互稱、開合呼應(yīng)等等藝術(shù)手段的辯證處理,使之處在一個(gè)激越跳動態(tài)勢中的”。我們從“百獸率舞”與“龍飛鳳舞”中可以看出,“飛動”之美是構(gòu)成華夏藝術(shù)特征的一個(gè)基本因素,對它的理解并不僅僅源于對鳥獸飛動之勢的機(jī)械模擬,而是變相地將其形式化、抽象化,繼而程式化了。因此中國的繪畫、戲劇、書法都具有了共同的特征。
具體而言,它既保留了華夏藝術(shù)“飛動”之美的“樂舞精神”,又承傳并修正了以“管弦伎樂,特善諸國”而著稱的龜茲樂舞等,從而以視覺藝術(shù)的形式傳達(dá)出聽覺的美妙意境,以空間的藝術(shù)畫面表現(xiàn)了時(shí)間的韻律,以靜態(tài)的人物形象展示出動態(tài)的曼妙樂律,走出了一條美輪美奐的審美之路。
二、“飛動之美”的具體體現(xiàn)
敦煌壁畫的“飛動之美”體現(xiàn)在壁畫的方方面面,它蘊(yùn)含在整體的空間內(nèi)部。就此,我們主要從三個(gè)大的方面來加以論述,即人物形象、線條韻律、裝飾圖案。
(一)人物形象
敦煌壁畫主要是以經(jīng)變、本生、佛傳及因緣故事等佛教內(nèi)容為主導(dǎo),所以壁畫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是人們供奉的佛陀、菩薩、弟子、天神、飛天神仙及其說法像等。人物的形象在其壁畫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飛天為例,其形象在敦煌壁畫中幾乎每個(gè)洞窟都有描繪,不同時(shí)期的造型也各部相同,但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視覺的飛動之感。如,莫高窟第251,260窟北魏時(shí)期的飛天,飛翔姿態(tài)多種多樣,有的橫游太空,有的振臂騰飛,有的合手下飛,氣度豪邁大方,勢如翔云飛鶴。飛天起落處,朵朵香花飄落,頗有“天花亂墜滿虛空”的詩意。
(二)線條韻律
線條是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一種重要的表現(xiàn)形式,用線來表現(xiàn)是人們觀看方法的一種具體體現(xiàn)。在敦煌壁畫中,無論是 “曹衣出水”(莫高窟第254窟彌勒佛像),還是“春蠶吐絲”(莫高窟第263、272窟中的早期人物線描)都成為了其藝術(shù)之美的載體與形象構(gòu)成。各種線條極其富有韻律,在抑揚(yáng)頓挫、行云流水般的筆法運(yùn)轉(zhuǎn)中,突出了神態(tài)逼真、氣韻生動的藝術(shù)形象,讓我們感到其生命的存在――運(yùn)動。
敦煌壁畫中的線條使用范圍涉及方方面面,如莫高窟第257窟之北魏壁畫鹿王本生故事中的水紋線描;第285窟西魏壁畫中的行云,東、北二壁的秀骨清像人物、伎樂天;第249窟窟頂白描畫群豬圖;第249窟窟頂南北二披西魏壁畫中的東王公、西王母,乘龍車鳳輩攜帶天神仙人遨游天界,四周錦旗飛揚(yáng),再如第428窟北周的供養(yǎng)人圖等等。從人物到裝飾圖案、山水、花鳥無不流動著一種“飛動”之感。
(三)裝飾圖案
在敦煌藝術(shù)中壁畫是附著建筑并服務(wù)于彩塑佛像這一中心,但它實(shí)際上構(gòu)成了視覺藝術(shù)的主要部分。與此相類,壁畫中的圖案也同樣如此。雖然它從屬于壁畫,但實(shí)際上起到了將建筑、雕塑、壁畫連成一體的作用。換言之,建筑、雕塑與壁畫都是依靠圖案的裝飾效應(yīng)而構(gòu)成完整的有機(jī)體。圖案種類繁多,爭氣斗艷,花樣別出。例如,藻井、邊飾、服飾、背光、植物、華蓋、垂幔等等。其中除了藻井的裝置略顯嚴(yán)謹(jǐn)之外,其它的圖案都隨著壁畫的意境“滿壁風(fēng)動”。如,莫高窟257窟的天人化生火焰紋佛背光,佛身光為五重光環(huán),繪天人與火焰紋。火焰紋中有一環(huán)為一開一合的波狀單線火焰紋,整體造型像一團(tuán)火焰在空中飛舞;第296窟忍冬蓮花禽鳥紋邊飾,邊飾中繪有蓮花、鴿子、摩尼寶,表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佛教徒向往自然的心境,整個(gè)邊飾在統(tǒng)一的姿態(tài)中冉冉升起。
敦煌壁畫的“飛動”在其它方面也有體現(xiàn),如屋頂?shù)那€,向上微翹的飛檐,使這個(gè)本應(yīng)是異常沉重的往下壓的大帽,反而隨著形的曲折,顯出向上挺舉的飛動輕快之感。再如統(tǒng)一色調(diào)下的色彩變化都可以展示出“天衣飛揚(yáng),滿壁風(fēng)動”的飛動之美。
三、“飛動之美”的思想底蘊(yùn)
敦煌壁畫中“飛動之美”的藝術(shù)滲透著濃厚的樂舞韻味,以空間的、靜態(tài)的造型藝術(shù)來表達(dá)時(shí)間的、動態(tài)的表演藝術(shù),正是敦煌藝術(shù)的不傳之秘。敦煌壁畫的“飛動之美”它主要取決于一種獨(dú)特的世界觀,如,敦煌壁畫中的飛天等伎樂形象不僅有佛性的因素、中華藝術(shù)線描技藝之功,以及飛動的衣服視覺等,更主要取決于源自本土文化的哲學(xué)根源,“天人合一”的思想底蘊(yùn)。這種獨(dú)特的思維方式是成為“飛動之美”的真正根源。
就此而言,柴劍虹先生認(rèn)為敦煌壁畫上“飛天”正出于此。他說:“從根本上主張儒、釋、道相通的李唐天子及當(dāng)時(shí)的思想家們,是連接‘天’與‘人’的橋梁,是注釋‘天’、‘人’關(guān)系的權(quán)威;而‘天人合一’的觀念,則在由普普通通的畫匠所描繪的折射宮廷與民間生活的佛教壁畫中得到了反映”。飛天形象從而經(jīng)歷了由神到人、從天上到人間的清晰線索,“不僅僅是審美意識的變化,也是哲學(xué)觀念的演進(jìn)――人們對‘天’的認(rèn)識由朦朧到清晰逐漸加深,宗教崇拜日趨淡化,改造與服務(wù)人間社會的世俗需求日益強(qiáng)烈,隨之而來的是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結(jié)合更加緊密,這正是‘天人合一’觀念在藝術(shù)上具體而生動的體現(xiàn)”。
參考文獻(xiàn):
[1]易存國.敦煌藝術(shù)美學(xué)――以壁畫藝術(shù)為中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王大有.龍鳳文化源流[M].中國時(shí)代經(jīng)濟(jì)出版社,2008.
[3]李澤厚.美學(xué)三書[M].天津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3.
2013年1月,國務(wù)院批復(fù)在甘肅成立華夏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這是中國第一個(gè)國家級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平臺。按照國家關(guān)于甘肅發(fā)展的戰(zhàn)略定位和建設(shè)文化大省的總要求,甘肅省打破現(xiàn)有行政界限,統(tǒng)籌全省文化資源和各類生產(chǎn)要素,以文化建設(shè)為主題,以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戰(zhàn)略性調(diào)整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式根本性轉(zhuǎn)變?yōu)橹骶€,確定了圍繞“一帶”、建設(shè)“三區(qū)”、打造“十三板塊”的工作布局。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頂層設(shè)計(jì)已經(jīng)完成,平臺搭建基本到位,“一帶”“三區(qū)”“十三板塊”的各項(xiàng)工作有序推進(jìn)。
省委、省政府打造“敦煌畫派”、深化“朝圣·敦煌”甘肅畫院系列創(chuàng)作工程,是華夏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建設(shè)的重要組成部分。
“敦煌畫派”是個(gè)新概念,是一項(xiàng)繼承敦煌石窟藝術(shù)體系、絲綢之路文化遺產(chǎn)、彩陶文明和多民族文化傳統(tǒng),開宗立派的一個(gè)文化建設(shè)工程,帶有前瞻性的美術(shù)文化主張;是以敦煌為文化藝術(shù)活動的中心要素,探索構(gòu)建一個(gè)具有敦煌藝術(shù)特征的美術(shù)風(fēng)格,營造出一個(gè)既是傳統(tǒng)的又是現(xiàn)代的、既是守正的又是創(chuàng)新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研究體系。打造“敦煌畫派”是甘肅美術(shù)建設(shè)的需要,對建設(shè)文化大省和華夏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建設(shè),具有積極而深遠(yuǎn)的意義和作用。2012年,甘肅畫院經(jīng)過提出了“朝圣·敦煌——甘肅畫院美術(shù)創(chuàng)作工程”系列實(shí)施方案。方案核心是組織畫家自覺投身“美術(shù)敦煌”的學(xué)術(shù)研究和打造“敦煌畫派”系列美術(shù)創(chuàng)作實(shí)踐活動,將打造“敦煌畫派”落實(shí)到具體學(xué)術(shù)研究和創(chuàng)作實(shí)踐之中。此后,甘肅畫院所有業(yè)務(wù)活動都圍繞打造“敦煌畫派”和“朝圣·敦煌”活動展開,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取得初步成效。2013年3月,《絲綢之路》文化版策劃出版“回眸:2012年朝圣敦煌”專輯,對所取得的成果進(jìn)行總結(jié)和推介。
2013年,這項(xiàng)宏大的藝術(shù)工程進(jìn)行得更扎實(shí)、更理性、更有聲勢。甘肅畫院先后組織畫家開展“重走絲綢之路·佛教東漸”東線和西線考察、采風(fēng)、創(chuàng)作活動。畫家、書法家在甘肅、新疆、陜西等地實(shí)地考察歷史文化遺址,了解民俗風(fēng)情,用繪畫、圖像、文字等方式記錄沿途風(fēng)土人情,采集創(chuàng)作素材。每位畫家不但有了寫生作品、創(chuàng)作作品,還寫了豐富多彩的考察采風(fēng)日記,多方位、多層次展示他們的審美理想和藝術(shù)才華。與此同時(shí),甘肅畫院還鼓勵(lì)從事理論研究的同志,從學(xué)術(shù)理論界定、創(chuàng)作題材定位、創(chuàng)作技法風(fēng)格研究、代表性人物傳承延續(xù)等方面進(jìn)行深入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省文聯(lián)、省政府文史研究館聯(lián)合主辦了“段兼善畫展”, 共展出75幅作品,是作者近30年來對敦煌繪畫藝術(shù)創(chuàng)作成果的全面展示,也是首次將個(gè)展納入“朝圣·敦煌”創(chuàng)作工程。
2013年,“朝圣·敦煌”活動有了質(zhì)的飛躍和巨大變化,成果喜人。《絲綢之路》及時(shí)將畫家藝術(shù)狀態(tài)和創(chuàng)作成果向社會推介,無疑是這項(xiàng)文化工程的有益延伸,也為社會各界與藝術(shù)家架構(gòu)交流平臺。我們期望通過這些活動,使打造“敦煌畫派”和“朝圣·敦煌”活動更具群眾基礎(chǔ),更具民族特色,更具藝術(shù)魅力!
1 敦煌聯(lián)珠紋的形態(tài)特征
1.1 敦煌聯(lián)珠紋的概念
根據(jù)史料可考,敦煌聯(lián)珠紋一般是在多個(gè)銜接的雙線圓輪中畫上各種珍禽鳥獸。由于聯(lián)珠紋的獸類圖樣一般都以雙數(shù)出現(xiàn),且左右對稱,因此也有人稱它為聯(lián)珠對獸紋或連珠對鳥紋。除此之外,在聯(lián)珠紋雙線圓輪中還有許多均勻的圓珠,稱為聯(lián)珠;而畫在圓輪之間,大小相等,位置固定在四處聯(lián)接點(diǎn)中間的,稱為聯(lián)珠紋圓輪。
從考古發(fā)現(xiàn)的大量波斯薩珊時(shí)期服飾織物、建筑雕塑、錢幣器皿上,隨處可見聯(lián)珠紋。也正是由于人們的喜愛,聯(lián)珠紋的發(fā)展成為了必然。它與民族文化息息相關(guān),成為了中亞民族藝術(shù)圖樣的代表之一。
1.2 敦煌聯(lián)珠紋的分類
誠如關(guān)友惠在《解讀敦煌敦煌裝飾圖案》中的概括:從唐至元的這一時(shí)期,敦煌裝飾紋樣發(fā)展的脈絡(luò)清晰,承襲關(guān)系明確,并影響到明、清乃至近代[2]。他指出,敦煌聯(lián)珠紋自北魏傳入開始逐漸融合中國文化特征。隋代統(tǒng)一后,敦煌聯(lián)珠紋進(jìn)一步融入中原。發(fā)展到盛唐,敦煌聯(lián)珠紋的紋樣開始富于變化。到了中唐和晚唐,由于敦煌先后被吐蕃和張氏歸義軍占領(lǐng),聯(lián)珠紋轉(zhuǎn)而走清雅平穩(wěn)的路線。至宋朝以及蒙元時(shí)期,受各方政權(quán)拉鋸和宗教藝術(shù)影響,紋樣形式逐漸向漢式建筑彩畫靠攏。在西夏及元時(shí)期,聯(lián)珠紋則受宋遼裝飾圖樣的影響,以神獸花鳥為主。根據(jù)關(guān)友惠的分析和實(shí)際敦煌壁畫紋樣,不難發(fā)現(xiàn)敦煌聯(lián)珠紋的分類主要涉及到題材、造型和構(gòu)造,下面就從這幾個(gè)方面進(jìn)行具體解析。
1.2.1 題材的分類
敦煌聯(lián)珠紋的紋樣題材分類,主要是從單一到豐富,涵蓋了中亞風(fēng)俗的題材內(nèi)容,有鮮艷繁麗的花卉禽獸,大氣穩(wěn)重的伽陵頻迦鳥等祥瑞紋樣,還有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相近的生活實(shí)景和花鳥植物等。
1.2.2 構(gòu)造的分類
敦煌聯(lián)珠紋的紋樣結(jié)構(gòu)分類,主要是從簡單的聯(lián)珠圈環(huán)繞,與環(huán)形、菱形、直線形、方形等中國傳統(tǒng)紋樣進(jìn)行多種組合形式。
1)環(huán)形結(jié)構(gòu)中的聯(lián)珠紋。敦煌隋代洞窟中環(huán)形背光結(jié)構(gòu)中的裝飾紋樣絕大部分都繪有聯(lián)珠紋,而且表現(xiàn)形式多樣,環(huán)形聯(lián)珠紋通常能夠展示某種精神文化或場景內(nèi)容,不同于初唐時(shí)期的散裝聯(lián)珠,相對表現(xiàn)性上更顯得嚴(yán)謹(jǐn)與典雅。
2)菱形結(jié)構(gòu)中的聯(lián)珠紋。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隋朝的聯(lián)珠紋也被中亞、波斯織錦圖案所影響,出現(xiàn)了菱形結(jié)構(gòu)的聯(lián)珠紋。如菩薩身上的服飾裝飾紋樣常有菱格紋樣,以黑色作為底色,上面描繪淺色的曲線和白色的聯(lián)珠紋,并有金線作為點(diǎn)綴,青色的鳳凰張開雙翅,動態(tài)優(yōu)美飽滿,色彩炫麗奪目。
3)直線排列的聯(lián)珠紋。直線排列的聯(lián)珠紋一般出現(xiàn)在西域繪畫和中國織造的各種聯(lián)珠紋織錦中,如聯(lián)珠蓮花紋就是直線排列的聯(lián)珠紋邊飾中常見的紋樣,在這之中又體現(xiàn)著多彩與豐富的內(nèi)涵。隋代401窟西壁龕沿蓮花聯(lián)珠紋見圖1,邊飾赭紅底,青環(huán)白珠,蓮花有四瓣盛開狀,六瓣含苞待放狀,如同云紋狀,是最活潑的蓮花聯(lián)珠紋。雖然織錦中有的條形聯(lián)珠紋樣還附加了西域的文化信仰元素,但是這部分元素在隋代敦煌洞窟中幾乎已經(jīng)全部簡化和省略了,只表現(xiàn)出聯(lián)珠紋單純的中國化裝飾美。
4)方形結(jié)構(gòu)中的聯(lián)珠紋。方形結(jié)構(gòu)中的聯(lián)珠紋,對起到豐富整個(gè)藻井有著出色的表現(xiàn)力。第393窟覆斗藻井見圖2,井心畫盤莖蓮花,井心與周邊裝飾聯(lián)珠紋樣形態(tài)比較統(tǒng)一,不再沿襲繁復(fù)的隋初風(fēng)格,而傾向于隋末的簡潔畫風(fēng),此窟的聯(lián)珠紋樣與藻井相得益彰。
2 敦煌聯(lián)珠紋在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現(xiàn)狀
從概念上來說,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是近代經(jīng)濟(jì)規(guī)律下衍生的一種商業(yè)手段,它需要最科學(xué)、最新穎、最具有創(chuàng)意的元素不斷加入,來促進(jìn)和保證它的實(shí)效性,因此,敦煌聯(lián)珠紋的應(yīng)用符合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的本質(zhì)屬性。其應(yīng)用主要涉及兩種類型,即環(huán)形動物聯(lián)珠紋和直條形邊飾聯(lián)珠紋,從圖形、文字、色彩到視覺形象等觸及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的多個(gè)基本構(gòu)成,應(yīng)用范圍不設(shè)限,且得到受眾的廣泛認(rèn)可和喜愛。
2.1 環(huán)形動物聯(lián)珠紋的應(yīng)用
環(huán)形動物聯(lián)珠紋在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往往可以實(shí)現(xiàn)一種思想意識的主觀性傳播,并產(chǎn)生一種視覺審美的愉悅感,因此,環(huán)形動物聯(lián)珠紋元素常被用于現(xiàn)代圖形設(shè)計(jì)和圖像符號設(shè)計(jì)等。
蜂蜜手工肥皂的產(chǎn)品設(shè)計(jì)見圖3,將蜜蜂的形象繪制于環(huán)珠中央,周圍綴以輔的文字和圓點(diǎn)裝飾,表達(dá)出一種純天然原生態(tài)的視覺暗示。這款設(shè)計(jì)圖樣從構(gòu)圖到元素運(yùn)用都與敦煌聯(lián)珠紋中的環(huán)形動物聯(lián)珠紋如出一轍,若與隋代西壁龕沿的翼馬聯(lián)珠紋邊飾對比,可見兩者設(shè)計(jì)之間的共通性。而需要注意的是,諸如此類的動物聯(lián)珠紋運(yùn)用和概念傳達(dá),關(guān)鍵還在于環(huán)形聯(lián)珠紋中間的動物紋樣或其他意象紋樣的選擇是否能夠承載設(shè)計(jì)意圖。
2.2 直線形邊飾聯(lián)珠紋的應(yīng)用
直線形邊飾聯(lián)珠紋在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兼顧了實(shí)用功能和裝飾功能。例如,作為實(shí)用功能的延伸,直線形邊飾聯(lián)珠紋被融入到結(jié)構(gòu)線劃分之中,通過其自身圖樣屬性和搭配方式的多變性,起到了既界定鮮明又自然連貫的效果。
楊桃音樂會海報(bào)設(shè)計(jì),就通過波點(diǎn)紋與純色塊的差異性凸顯了主題文字,在簡單直接的信息傳達(dá)與跳躍活潑的視覺沖擊之間過渡得流暢自然。這樣的設(shè)計(jì)效果正是發(fā)揮了直線形邊飾聯(lián)珠紋的結(jié)構(gòu)屬性,將背景與主題劃分鮮明且服帖融合。同時(shí),作為裝飾功能的應(yīng)用,直線形邊飾聯(lián)珠紋也被融入窗簾床單等家紡的邊飾中,通過創(chuàng)意搭配的圖樣設(shè)計(jì),達(dá)到豐富有趣的裝飾效果。
3 敦煌聯(lián)珠紋在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原則、策略和價(jià)值
3.1 體現(xiàn)民族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原則
在敦煌聯(lián)珠紋的設(shè)計(jì)應(yīng)用中,在追求形似時(shí)也不能忽略神似。雖然在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應(yīng)用中強(qiáng)調(diào)全球化視角,但是不可否認(rèn)的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始終是亟待傳達(dá)的文化內(nèi)涵。如果設(shè)計(jì)師能夠從對敦煌聯(lián)珠紋的運(yùn)用中獲得靈感,以不拘泥的豐富形式,在作品中滲透民族文化和情感,為現(xiàn)代人的生活增添傳統(tǒng)文化色彩,那便是一種至高的藝術(shù)境界。
3.2 傳統(tǒng)圖形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原則
敦煌聯(lián)珠紋是隨著中亞民族遷徙而來的一種紋樣,基于中國民族文化的豐富性和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敦煌聯(lián)珠紋的造型題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擴(kuò)展。它既具有中亞藝術(shù)的風(fēng)貌,又兼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基礎(chǔ),具有不可替代的藝術(shù)價(jià)值。
在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中,設(shè)計(jì)師往往并不欠缺設(shè)計(jì)能力,而是欠缺一種對于文化信念的堅(jiān)守和民族思想的自覺。許多在國際上享有盛譽(yù)的成功中國設(shè)計(jì)師,往往在其優(yōu)秀的設(shè)計(jì)作品中貫徹了一種強(qiáng)大的人文精神,演繹出傳統(tǒng)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所以說,在敦煌聯(lián)珠紋的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應(yīng)用中也需要本著這樣對繼承和創(chuàng)新的應(yīng)用原則,創(chuàng)造符合時(shí)代特征的全新視覺效果的設(shè)計(jì)作品。
3.3 迎合時(shí)代特征和審美追求原則
消費(fèi)早已不是一種單純的物物交換,其中蘊(yùn)含了意義消費(fèi)的概念。產(chǎn)品和品牌的附加值集中體現(xiàn)在其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中,由此,設(shè)計(jì)的有效性也被日漸凸顯。設(shè)計(jì)作品迎合現(xiàn)代審美情趣,體現(xiàn)時(shí)代感已然成為一種評判標(biāo)準(zhǔn)。
肥皂工廠香皂包裝,運(yùn)用了敦煌聯(lián)珠紋的現(xiàn)代構(gòu)造方式,既展現(xiàn)了屬于民族文化的審美情趣,又符合時(shí)代特征,清晰地凸顯了傳統(tǒng)典雅的意蘊(yùn)。當(dāng)大眾開始傾向于接納民族文化意象,巧妙地運(yùn)用傳統(tǒng)文化符號進(jìn)行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已經(jīng)成為一種設(shè)計(jì)共識。敦煌聯(lián)珠紋是敦煌文化的代名詞,能夠引發(fā)受眾對于敦煌文化的心理共鳴和審美感動,因此聯(lián)珠紋的設(shè)計(jì)應(yīng)用要符合受眾物質(zhì)和精神的雙重需求。
3.4 敦煌聯(lián)珠紋在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價(jià)值
敦煌聯(lián)珠紋的存在與發(fā)展,是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融基礎(chǔ)上的藝術(shù)表征,而敦煌聯(lián)珠紋所受到的關(guān)注和擁護(hù),正是國人文化審美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其在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價(jià)值體現(xiàn)。
3.4.1 加強(qiáng)視覺傳達(dá)的審美共鳴
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是一種關(guān)于發(fā)起者如何向接受者傳達(dá)信息的設(shè)計(jì)語言,它是商品與受眾之間的傳話者,交換彼此的意見與信息。從視覺傳達(dá)的定義,不難發(fā)現(xiàn)傳達(dá)的關(guān)鍵在于溝通,因此,選擇一個(gè)合適的平臺和合適的設(shè)計(jì)意象是建立溝通的關(guān)鍵,更是完成視覺傳達(dá)的關(guān)鍵。這種共通的視覺心理,能更生動、更直觀地將敦煌文化概念和聯(lián)珠紋元素植入設(shè)計(jì)作品,在視覺傳達(dá)中引發(fā)受眾的審美共鳴,使受眾在作品中感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細(xì)膩觸感,實(shí)現(xiàn)傳播的目的。
3.4.2 增強(qiáng)視覺傳達(dá)的民族性
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是一門緊跟時(shí)代潮流的學(xué)科,它不僅需要較強(qiáng)的專業(yè)能力與豐富的學(xué)科知識,還需要敏銳的全球性時(shí)尚觸覺。因而,大多數(shù)設(shè)計(jì)師設(shè)計(jì)出來的作品都較為時(shí)髦前衛(wèi),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設(shè)計(jì)的民族性。
筆者設(shè)計(jì)的雙燈品牌系列紙巾包裝,采用邊飾聯(lián)珠紋的組合應(yīng)用,打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視覺符號。敦煌聯(lián)珠紋深厚文化底蘊(yùn)和豐富多變的素材元素,為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極大的自由度與隨意感,能夠激發(fā)出廣闊的想象空間,讓每個(gè)人都能依照作品的需要和個(gè)人的喜好任意發(fā)揮,自由表達(dá)。聯(lián)珠紋的設(shè)計(jì)應(yīng)用能夠展現(xiàn)出十足的藝術(shù)感染力,能夠很好地傳達(dá)出設(shè)計(jì)內(nèi)涵,并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與視覺傳達(dá)的創(chuàng)意靈感有機(jī)結(jié)合,在為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添加民族元素的同時(shí),也為民族文化注入創(chuàng)新精神。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期刊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xué)會;首都師范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香港大學(xué)饒宗頤學(xué)術(shù)館;北京大學(xué)東方學(xué)研究院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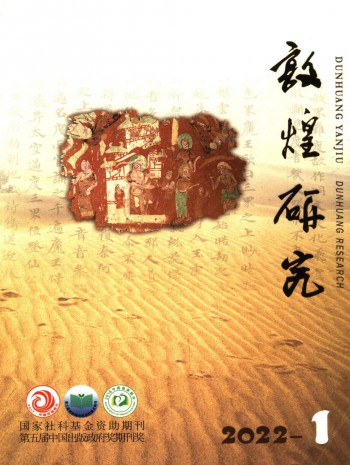
預(yù)計(jì)1-3個(gè)月審稿 CSSCI南大期刊
甘肅省文化和旅游廳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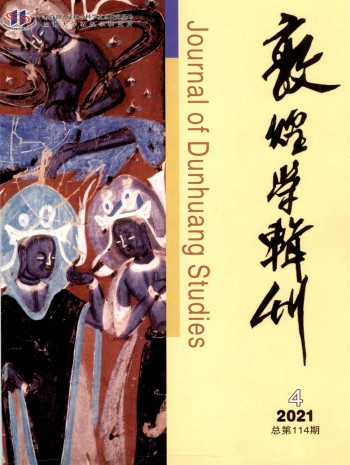
預(yù)計(jì)1-3個(gè)月審稿 CSSCI南大期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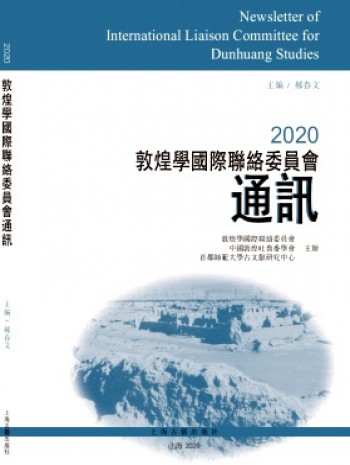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期刊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xué)會;首都師范大學(xué)古文獻(xiàn)研究中心;敦煌學(xué)國際聯(lián)絡(luò)委員會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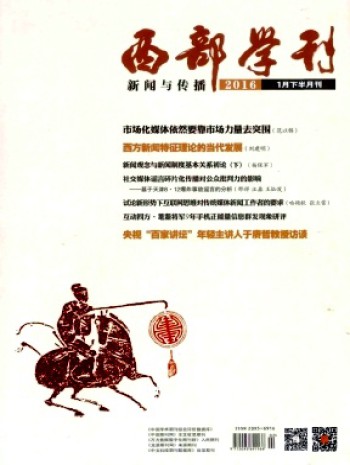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期刊
陜西新華出版?zhèn)髅郊瘓F(tuán)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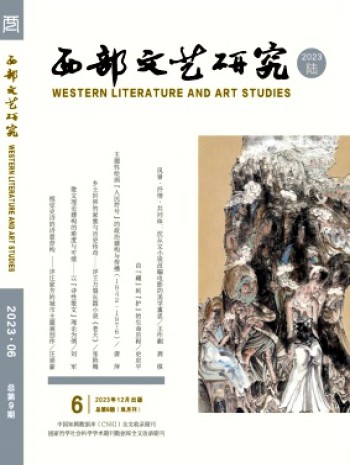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期刊
甘肅省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