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shí)間:2023-08-09 17:23:08
引言:易發(fā)表網(wǎng)憑借豐富的文秘實(shí)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電子音樂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內(nèi)容,可隨時(shí)聯(lián)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guān)鍵詞:電子音樂、啟示
此次音樂周共五天,包括6場(chǎng)音樂會(huì)、10個(gè)系列普瑞馬斯工作坊、6場(chǎng)相關(guān)講座以及3天的國際論壇,其中有以上作曲家的作品音樂會(huì)、新生代的作品音樂會(huì)及非學(xué)院派作品音樂會(huì)等。“電子音樂(electronic music)可以泛指一切利用電子手段產(chǎn)生、修飾的聲音制作而成的音樂,與由共鳴體自然發(fā)音的音樂相區(qū)別。”[1]電子音樂產(chǎn)生于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但電子音樂的教學(xué)產(chǎn)生于二十世紀(jì)四、五十年代。電子音樂也有人稱之為噪音音樂。電子音樂的音響沖破了傳統(tǒng)樂器的演奏及音響概念,嚴(yán)格地說,電子音樂不是傳統(tǒng)樂器演奏的,也不是傳統(tǒng)音高、旋律、調(diào)性、和聲、節(jié)奏等技法的運(yùn)用,更不是當(dāng)代電聲樂器的概念,而是在實(shí)驗(yàn)室里運(yùn)用電子設(shè)備,采樣、錄音、制作,利用各種音響進(jìn)行作曲。
一、電子音樂暨計(jì)算機(jī)音樂綜述
電子音樂的發(fā)展從1948年法國作曲家謝菲爾(Schaeffer)的第一首電子音樂作品《火車練習(xí)曲》開始[2],經(jīng)歷了錄音帶音樂和合成器音樂二個(gè)發(fā)展階段。而在電子音樂相當(dāng)普及的今天,計(jì)算機(jī)音樂(computer music)已經(jīng)是電子音樂的主流。“計(jì)算機(jī)音樂是指那些不僅利用計(jì)算機(jī)作曲而且其音響材料也出自計(jì)算機(jī)的電子音樂作品。”[3]確實(shí)如此,當(dāng)今,電子音樂從構(gòu)思、設(shè)計(jì)、創(chuàng)作、制作、播放及演奏無一不在計(jì)算機(jī)平臺(tái)上,來自荷蘭海牙的吉斯•塔澤拉教授重點(diǎn)地闡述了這一點(diǎn)。他在《個(gè)人創(chuàng)作策略與作品展示》的論壇中詳細(xì)的解釋了電子音樂與傳統(tǒng)音樂的異同,傳統(tǒng)音樂無論如何都是有著音高、旋律以及和聲等因素,而電子音樂則不是,而是非音高有的是大自然的各種聲音,有的甚至是噪音的組合。他的實(shí)驗(yàn)室從1996年開始做計(jì)算機(jī)的創(chuàng)作、研究工作,以前的電子音樂音響的制作都是物理的模擬音樂制作設(shè)備,當(dāng)今計(jì)算機(jī)的廣泛使用早已淘汰與代替了原來的模擬音樂實(shí)驗(yàn)室。計(jì)算機(jī)有著產(chǎn)生各種聲音的巨大的可能性;有著利用各種軟件制作復(fù)雜節(jié)奏與豐富音響的能力,并且可以簡(jiǎn)化電子音響的制作過程和提高效率,有時(shí)只需簡(jiǎn)單改變一些菜單“指令”,就能變化出多種同首作品不同的音響演示版本,甚至?xí)霈F(xiàn)意想不到的特殊音響效果。計(jì)算機(jī)平臺(tái)上的電子音樂制作所展示的廣闊前景,人們還難以預(yù)料,還有待致力于電子音樂創(chuàng)作的作曲家們不斷去挖掘。
二、電子音樂有感
這次上海音樂學(xué)院電子音樂國際音樂周同時(shí)也進(jìn)行了為期五天的論壇與專家講座。其中2009.10.22日上午由武漢音樂學(xué)院劉健教授題為《電子音樂中音響主體的東方特制》的論文為與會(huì)的國內(nèi)專家教師留下了較深刻印象和啟示。這其中劉健教授一是主要談到電子音樂創(chuàng)作是否需要“主題”,他談到為了鮮明地表達(dá)音樂作品表現(xiàn)的目的,并且為創(chuàng)作音樂發(fā)展所提供的素材和材料,是需要設(shè)立一個(gè)創(chuàng)造主題的;二是變換創(chuàng)作技法,如運(yùn)用一個(gè)較長的過程來逐漸發(fā)展并揭示出音樂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目的而發(fā)展成的電子音樂作品,這樣的創(chuàng)作是不需要主題的。這些技法的作品在“非學(xué)院派電子原生”音樂會(huì)上有具體的體現(xiàn)。如其中一首作品是一種節(jié)奏×× ×× ∣0××× ×× 的電子“噪音”重復(fù),若干小節(jié)后加入了不協(xié)和的音高,又進(jìn)行了若干小節(jié)后,它的節(jié)奏和音高開始逐漸地加厚、加濃、速度加快、音響同時(shí)逐漸產(chǎn)生變化形成無主題的電子音樂作品;另外一首是作品一開始,只有一只小蟲子微弱地在鳴叫,然后逐步地將鳴叫加多,意味著聲部的加厚,最后到有眾多蟲子的鳴叫。還有一首作品純屬是電流噪聲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強(qiáng)、聲部由薄到厚的音響作品。
劉健教授還談到,電子音樂和東方元素特制相互契合的問題。當(dāng)使用音響材料并想構(gòu)成具有主體內(nèi)涵的樂隊(duì)時(shí),西方作曲家開始用音響的方式,而不是用音高的方式來思考問題時(shí),這種狀態(tài)就已經(jīng)接近了東方音樂的思維模式,并且使構(gòu)成的某些主體元素具有了中國民族音樂的“音腔”式特征。“音腔”的概念是沈洽在他的《音腔論》中提出的。中國民族音樂的旋律可在每一個(gè)音上做到包括音高、力度、音色的細(xì)微量變,形成曲線音感。而西方音樂如鋼琴它是運(yùn)用音高來組合音樂的,沒有音高、音色的細(xì)微量變。那么如何構(gòu)成“音腔”特征呢?前提是作曲家希望有音味的主題;用不同的音響材料來區(qū)別主題的不同階段,在技法上主要運(yùn)用拼貼的手法等;用長音逐漸加強(qiáng)音高的方式來替代重音點(diǎn),并使得音階段落有所變化,在技法上主要運(yùn)用電子設(shè)備進(jìn)行調(diào)制變相的技術(shù)等。這個(gè)課題也是專業(yè)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研究。
【關(guān)鍵詞】 薩頂頂;超功利;天人合一;自語;多元化
[中圖分類號(hào)]J60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薩頂頂是一個(gè)無法用常規(guī)來定義的歌手。她的音樂交織著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民族唱法與電子聲完美融合的多種音樂元素。《萬物生》和《天地合》兩張唱片在全球的發(fā)行,不僅給她帶來了世界性聲譽(yù),同時(shí)也使得中國的流行音樂在整體上得到了改觀,將中國的流行音樂推向了一個(gè)新的高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薩頂頂對(duì)于當(dāng)前的中國流行音樂具有著“里程碑”的作用,誠如作曲家劉曉耕所說:“中國的樂壇上我們看到的是千人一面,都是一個(gè)模樣,一種聲音。這個(gè)其實(shí)會(huì)令人討厭。而她(薩頂頂)的聲音突然讓我發(fā)現(xiàn),怎么還有這樣唱歌,怎么還有這種語言。我雖然聽不懂她唱什么,但是她表達(dá)的音樂的信息,讓我的神經(jīng)觸動(dòng)。”(CCTV-10人物專訪)薩頂頂以其極富顛覆性和開創(chuàng)性的音樂特質(zhì),給我們展現(xiàn)出流行音樂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一、超功利的創(chuàng)作理念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美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表現(xiàn)為功利主義的價(jià)值取向。如《荀子·樂論》中就明確指出音樂的特殊社會(huì)作用:“樂合同”,音樂可以使人與人之間保持一種和諧的關(guān)系。同時(shí)它也有著“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風(fēng)易俗”的功用。這種觀念直接給后世的音樂創(chuàng)作帶來深刻影響,一直到近現(xiàn)代。在19世紀(jì)末,中國處于戰(zhàn)爭(zhēng)和社會(huì)大變革時(shí)期,強(qiáng)調(diào)音樂的社會(huì)功能,努力讓音樂發(fā)揮啟蒙作用、為時(shí)代服務(wù),幾乎是當(dāng)時(shí)音樂創(chuàng)作的風(fēng)尚。建國后,國內(nèi)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又使得音樂成為“階級(jí)斗爭(zhēng)與生產(chǎn)斗爭(zhēng)的武器”。時(shí)期,音樂僅僅是一種“政治聲音”。
改革開放后,逐漸寬松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以及經(jīng)濟(jì)的繁榮,使得傳統(tǒng)“嚴(yán)肅音樂”開始面臨著依托文化工業(yè)而飛速發(fā)展起來的“流行音樂”的極大沖擊。正如梁銘越先生所說,“由于人們已厭倦過去多年的說教音樂,取而代之的是通俗音樂的興起”[1]。20世紀(jì)80年代,一個(gè)全新的重感性價(jià)值、日常生活審美化、世俗化的社會(huì)環(huán)境逐漸形成,流行音樂也越來越成為迎合大眾文化心理需求的一個(gè)重要方面。“人們需要具有娛樂文化性質(zhì)的音樂來使自己獲得愉快。這種現(xiàn)象也一直保留至今,所以流行音樂的作者大多是為迎合大眾的文化心理而進(jìn)行創(chuàng)作,內(nèi)容多以日常生活、愛情的題材為主……”[2]
傳統(tǒng)音樂過于強(qiáng)調(diào)音樂的功利性,顯然不符合音樂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當(dāng)前流行音樂又過于強(qiáng)調(diào)其商業(yè)性與娛樂性色彩,這使得中國的音樂陷入一種發(fā)展困境。
薩頂頂音樂創(chuàng)作的突圍成功,無疑給當(dāng)今的中國流行音樂發(fā)展提供了極富價(jià)值的借鑒和參考。首先體現(xiàn)在創(chuàng)作理念上。薩頂頂?shù)膭?chuàng)作理念不僅是對(duì)于傳統(tǒng)功利主義創(chuàng)作美學(xué)的反叛,同時(shí)也是對(duì)于30余年來中國流行音樂的超越。薩頂頂不止一次地在訪談中說到:“當(dāng)去做藝術(shù)的時(shí)候,我們千萬不要有目的性地去做。”(《MOGO音樂專訪》傳奇女伶薩頂頂專訪)在她看來,最健康的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方式,是使自己沉浸在藝術(shù)的世界里。薩頂頂認(rèn)為,音樂應(yīng)該不為任何目的服務(wù),它只是一種不涉利害的自由的愉快,創(chuàng)作音樂就應(yīng)該避免那種帶著目的的不健康的方式。“我覺得藝術(shù)一旦帶有了目的性,可能就會(huì)變得不是你最終想要的那個(gè)東西,也不會(huì)是你希望它達(dá)到的那個(gè)高度。”薩頂頂如是說。
音樂創(chuàng)作的“無目的性”,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某種“合目的性”。拋開功利主義的創(chuàng)作理念,薩頂頂十分強(qiáng)調(diào)音樂與人的精神世界的溝通。她曾多次說明,《萬物生》是要給人帶來寧靜感,《天地合》則試圖傳達(dá)出一種喜悅感。薩頂頂認(rèn)為,音樂與人的精神世界是冥冥之中沒有任何目的地結(jié)合在一起的。薩頂頂將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感覺”擺在十分顯明的位置,她說:“藝術(shù)是某種感覺。”(雅燃獨(dú)家專訪薩頂頂)在創(chuàng)作一首歌時(shí),她首先從感覺上進(jìn)行定義,待感覺找到后,再把具體的內(nèi)容填加進(jìn)去。換句話說,“感覺”是首要的,而內(nèi)容其次。從這個(gè)意義上看,音樂的內(nèi)容首先就在于那種不依附于“具體歌詞”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也即體現(xiàn)為一種“合目的性”。實(shí)際上,我們可以將這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看作是康德“審美不涉利害”觀念在21世紀(jì)中國音樂創(chuàng)作的回響。
著名奧地利音樂學(xué)家愛德華·漢斯里克(Eduard Hanslick)在《論音樂的美》中指出:“音樂美是一種獨(dú)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這是一種不依附、不需要外來內(nèi)容的美,它存在于樂音以及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中。優(yōu)美悅耳的音響之間的巧妙關(guān)系,它們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和對(duì)抗、追逐和遇合、飛躍和消逝,——這些東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現(xiàn)在我們直觀的心靈面前,并且使我們感到美的愉快。”[3]49薩頂頂?shù)膭?chuàng)作理念在某種程度上與漢斯里克的表述十分接近。她在拒斥功利主義音樂觀念的同時(shí),十分注重捕捉樂音的感覺,并試圖將這種感覺延伸開來,使人聽了之后能從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中抽離出去,或者內(nèi)心產(chǎn)生一種微妙的變化。“音樂作品是有思想情感的人的精神所創(chuàng)造的,因此作品本身也有充滿精神和情感的高度能力。”[3]53薩頂頂?shù)囊魳匪o我們帶來的美的愉快,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漢斯里克所說的,是“與精神內(nèi)涵有著最密切的關(guān)系”[3]52。
二、深刻的精神內(nèi)涵
薩頂頂?shù)膬蓮埑诰駜?nèi)涵上有著一以貫之的承繼性。她以孫子《天倫》中的一段文作為其依據(jù),“天地合乃萬物生”,并認(rèn)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她說:“我覺得這一句話帶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思考,所以就用了《萬物生》為名。”她說,萬物生是宇宙間萬物的開始,是不可阻擋、生生不息的一種生命力。第二張“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愿意和身邊的事物相合,也能時(shí)刻提醒自己做人不要太驕傲,這是心態(tài)與理念的改變。”《萬物生》中,薩頂頂選取作為背景,運(yùn)用一些人和自然、和宗教的關(guān)系來表達(dá)對(duì)于信仰的思考。而在制作《天地合》時(shí),薩頂頂已在全球巡演了22個(gè)國家和地區(qū),在接觸過多樣的文化之后,她突然覺得:“與其讓人去思考,還不如讓人喜悅起來。”在她看來,喜悅很重要,它可以使人忘記很多的煩惱,可以解決一切矛盾和糾紛。這張唱片中,薩頂頂選擇了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一些元素和內(nèi)容,唱的是人和自然之間微妙的、美好的、喜悅的感情。
薩頂頂?shù)囊魳烦錆M了想象。沉浸于她的富于靈動(dòng)的歌聲當(dāng)中,我們似乎可以從所處的環(huán)境中抽離出去,眼前浮現(xiàn)起一系列美好而安寧的意象:萬物初開的蒙昧早晨、圣潔的唐拉雅秀、月光下的村莊、傣家的米酒、藍(lán)色的駿馬、裊裊的炊煙等等。她用音符構(gòu)筑了一個(gè)自由、仁愛、和諧的世界。我們只要閉上眼睛就仿佛能看見青山綠水、世外桃源。在那里,人們快樂簡(jiǎn)單,唱歌跳舞,敲著銅鑼,辛勤勞作。我們感受著這無限永恒的世界,與它相溶。
音樂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種“意味”在薩頂頂這里實(shí)際上就可以歸結(jié)為人與自然、與萬物之間的和諧。而這恰恰也正契合了中華文化傳統(tǒng)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的主要基調(diào),張世英先生認(rèn)為它“給中國人帶來了人與物、人與自然交融和諧的高遠(yuǎn)境界”[4]。這一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儒道兩家的哲學(xué)當(dāng)中。道家偏重“自然”,強(qiáng)調(diào)人要順應(yīng)自然,以天合天,不做違背自然本性之事。儒家偏重“人文”,強(qiáng)調(diào)“性天相通”、“天人合德”。它們都反映了人對(duì)于“天”,即大自然的一種依賴感與親和感。中國哲學(xué)從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角度來考察二者之關(guān)系,認(rèn)為人應(yīng)當(dāng)以自然界為精神家園,熱愛大自然,與萬物和諧共處。在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huì),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惡化到自然要威脅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地步,這是目前人類亟需解決的問題。中國的“天人合一”哲學(xué),對(duì)于由“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所引發(fā)的生態(tài)危機(jī),有著重要的補(bǔ)偏救弊作用。也許就如季羨林先生所言:“在今天,只有東方的‘天人合一’思想方能拯救人類。”[5]
然而,薩頂頂?shù)囊魳凡⒉粌H僅是對(duì)于傳統(tǒng)“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簡(jiǎn)單重復(fù),它同時(shí)也標(biāo)示出一種新的時(shí)代色彩。從薩氏的歌聲中,我們甚至能感受到一種新型的生態(tài)美學(xué)觀念,人類應(yīng)該以一種普遍共生的審美態(tài)度對(duì)待自然,同自然形成中和協(xié)調(diào)、共同促進(jìn)的關(guān)系。薩頂頂對(duì)于自然的尊重和贊美,恰恰也體現(xiàn)出一種“主體間性”的美學(xué)思想。
薩頂頂通過音樂來構(gòu)筑人與自然之間的美好和喜悅情感。她認(rèn)為語言(包括梵文)是人與自然的溝通和交流方式;音樂和靈感都是很自然的東西;而且她試圖尋找最切合自然本性的抒唱方式(包括自語);她對(duì)原始性的文化十分感興趣,深深地被少數(shù)民族的和自然一起生活的狀態(tài)所感染;她甚至明確表示自己向往原始社會(huì)的愛情,率性而天然。
薩頂頂在專輯《天地合》的扉頁這樣寫到:“暫且放下我們作為人類驕傲強(qiáng)勢(shì)的一面,慢慢地隨著呼吸去尋找天地初始時(shí)人與自然的那份和諧統(tǒng)一。”在她的歌聲中,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可以感受到她對(duì)于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拋棄。
三、獨(dú)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
薩頂頂?shù)囊魳繁憩F(xiàn)形式可以說是極為獨(dú)特的。她是“中國第一個(gè)用梵文演唱歌曲的人”,她會(huì)用梵語、漢語、藏語和“自語”四種方式進(jìn)行演唱,而其獨(dú)創(chuàng)的“自語”又是她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表現(xiàn)形式。薩頂頂善于從自然界的各種聲響中尋求一種音樂旋律的可能性,并主張從各種不同的語言中尋求無限可能的聲音張力,以此表達(dá)自己。對(duì)此,作曲家何訓(xùn)田做過如是評(píng)價(jià):“這個(gè)歌手最可貴的地方,在于她能夠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dá)自己的思想。而這個(gè)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人是用別人的方式來表達(dá)自己的思想,甚至用別人的方式表達(dá)別人的思想。”
關(guān)于從自然界中尋求音樂旋律。在薩頂頂看來,聲音是沒有極限的,而我們學(xué)習(xí)連聲的各種方法,“都是為了讓你找到你聲音的多種可能性”(快樂大本營09年5月23日專訪薩頂頂)。這樣的話,其實(shí)就完全可以把自己回歸自然,去模仿自然界的聲音,這個(gè)時(shí)候,你“可以是樂器,可以是動(dòng)物、一汪泉水、一朵小花,可以是各種東西……”(雅燃獨(dú)家專訪薩頂頂)。薩頂頂?shù)囊魳泛挽`感來源于自然,她甚至認(rèn)為,走在路上聽到的汽車聲音,包括生活中任何的聲音,都可能變成音樂的靈感,它們都是一種自然的積累。如此一來,聲音的塑造性將打開到一個(gè)極為寬廣的層面,自然界的所有聲音都可以成為音樂里的可能性,并運(yùn)用到音樂里。如《錫林河邊的老人》中就有模仿羊叫的音響效果,這種聲音是經(jīng)過歌者精心創(chuàng)作出來的,被有意識(shí)地編配在音樂作品的整體中,體現(xiàn)出一種創(chuàng)造性因素。
關(guān)于運(yùn)用不同的語言進(jìn)行表達(dá)。任何一種語言都有著自身的發(fā)音系統(tǒng)和結(jié)構(gòu),就如薩頂頂所言,每一種語言的內(nèi)部節(jié)奏及音序都不同。當(dāng)要借助語言進(jìn)行演唱時(shí),就必然要尊重語言內(nèi)部的機(jī)制。如果要盡可能地?cái)U(kuò)容音樂中的聲響效果,采用多種語言進(jìn)行演唱無疑將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作為一個(gè)可以用梵語和藏語演唱歌曲的歌者,薩頂頂坦言,用梵語和藏語演唱,并不意味著自己就精通它們,“……最重要的是我發(fā)現(xiàn)了很多文字中都蘊(yùn)含著旋律,我敢于把這些旋律用原本的語言表達(dá)出來”,“選擇不同的語言演繹主要是因?yàn)楫?dāng)中有不同的情感”。正是觸摸到了不同語言內(nèi)部的旋律,同時(shí)又“希望還給音樂它最本質(zhì)的功能”,薩頂頂于是選擇了一種別人聽不懂的語言來演唱,如梵語的《萬物生》,藏語的《媽媽天那》。事實(shí)證明,這種實(shí)驗(yàn)性的操作具有著它的可行性。聽者雖然聽不懂薩頂頂所唱的歌詞內(nèi)容,但是她的音律一樣能打動(dòng)人。薩頂頂?shù)倪@一探索正是要告訴聽者,音樂是沒有語言界限的,我們?cè)诓欢谜Z言的前提下,照樣可以實(shí)現(xiàn)精神上的溝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薩頂頂所運(yùn)用的多種語言都屬東方語系。她認(rèn)為,“東方很多文字中,傳達(dá)出一種神秘、遙遠(yuǎn)的東西,一些不同于現(xiàn)實(shí)層面、物質(zhì)層面的東西”。而這也正是薩頂頂音樂中所追求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對(duì)此,法國音樂家艾瑞克評(píng)價(jià)說:“我雖然不是很理解(她的歌詞),但是中國那種感覺和歌曲的聲音,對(duì)我來說像魔法一樣,仿佛她的聲音來自另外一個(gè)星球!”
關(guān)于自語。薩頂頂將其視作為是一種“藝術(shù)觀點(diǎn)”。她說:“自語演唱是我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新的演唱形式,是我獨(dú)有的音樂,我在自己獨(dú)有的音樂中創(chuàng)造著自己,主宰著自己,表達(dá)著自己,我的音樂里面只有我自己的影子。”確實(shí),自語是薩頂頂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表現(xiàn)形式,她在訪談中都特別會(huì)談到這一點(diǎn)。在她看來,自語無需用任何現(xiàn)成的語言作為歌詞,而是隨著自己的心意,咿咿呀呀地吟唱。這種獨(dú)特的“自語”式演唱,以無意義的隨興哼唱表達(dá)自己情緒,來期待心與心的純粹交流和感動(dòng)。薩頂頂說,自語并不是胡言亂語,“這是我的一個(gè)想法,就是人們往往說話,語言到了一個(gè)層面之后,感情濃烈到一個(gè)程度,語言就有限了”(CCTV-10人物專訪)。自語是超越任何語言的音樂情感的自然流淌,這也被薩頂頂認(rèn)作是最初的、最樸質(zhì)的情感表達(dá)方法。她認(rèn)為,每一個(gè)人在沒有學(xué)會(huì)復(fù)雜語言的孩童時(shí)期,都會(huì)經(jīng)歷一個(gè)最原生態(tài)的階段。那個(gè)時(shí)候的情感是不受任何理性的、復(fù)雜的語言體系的束縛,因而也更加純真和直接。這種獨(dú)特的表現(xiàn)方式突破了歌詞所陷入的局限,它完全是一種即興發(fā)揮的偶然性音樂,“它本身的產(chǎn)生,就是很即興、很意外的”。聽者根本無法聽懂薩頂頂自語中所演唱的內(nèi)容,然而,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歌詞呢?相反,沒有歌詞,人的想象力完全得到釋放,這也使得薩氏音樂充滿了無窮的意義張力。在談到《錫林河邊的老人》時(shí),她說,當(dāng)唱道“我的外婆,白云捎去我的歌聲”時(shí),竟感到歌詞是如此蒼白,“太有束縛感了,它束縛了我的想象和回憶”。于是,薩頂頂決定放棄歌詞,用自語抒發(fā)感情。與之類似的如《希然寧泊》、《拉古拉古》、《云云南南》等歌曲,都是運(yùn)用了一些非語義性的音符進(jìn)行演唱。薩頂頂通過這些努力告訴我們:“語言和交流溝通,其實(shí)根本不需要符號(hào),更多的需要心與心的對(duì)應(yīng)。”人們完全可以忽略掉歌詞,讓自己的內(nèi)心融入音樂。這種富于探索性的演唱方式,更是被環(huán)球唱片亞太地區(qū)總裁Max Hole稱為“與神交流的語言”。
薩頂頂是一位真正自由的歌者,她把自己對(duì)于音樂的體會(huì)通過一種最為獨(dú)特的表現(xiàn)方式演繹了出來,她的音樂超越了概念的框定和語言的界限,她用自己獨(dú)特的表現(xiàn)形式帶給了聽者以精神上的享受。薩頂頂說:“……藝術(shù)是需要不斷創(chuàng)新的,而真正的藝術(shù)家就是要在藝術(shù)上開創(chuàng)一個(gè)新的時(shí)代,引領(lǐng)出一種新的藝術(shù)形式,并且把這種藝術(shù)形式充分地展現(xiàn)出來,讓大眾都從這種藝術(shù)形式中得到享受。”她做到了。
四、多元化的音樂元素
薩頂頂?shù)囊魳分薪豢椫鴤鹘y(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民族唱法與電子聲完美融合的多種音樂元素。對(duì)此《觀察家報(bào)》做出評(píng)價(jià)說,薩頂頂?shù)摹耙魳妨钊梭@艷,她融合了細(xì)致優(yōu)雅的東方民族旋律與西方的節(jié)奏和電子音樂”。就傳統(tǒng)意義而言,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民族與世界之間是一種對(duì)立性存在,而薩頂頂致力于消除這種對(duì)立,實(shí)現(xiàn)融合,并借此展示出音樂元素的多元化并存。
首先看傳統(tǒng)東方元素。薩頂頂?shù)囊魳飞钌畹卦谥袊奈幕寥溃硎鞠M讶诤细鱾€(gè)民族音樂的大中華文化背景介紹給聽眾,要將中國古老文化的精髓通過音樂的方式帶到全世界。“我歌曲的靈魂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正是在這樣一種清醒自覺的民族性自主意識(shí)的支配下,薩頂頂“蟄伏四年,游歷各國采風(fēng)”,以此來為自己的音樂創(chuàng)作汲取充足的養(yǎng)分。在她看來,亞洲的音樂在西方音樂面前很不自信,在這種情況下,薩頂頂毅然決定開發(fā)出自己獨(dú)特的音樂。她揮起民族古老文化的大旗,給世界音樂帶去東方神秘的色彩。“我要打入他們(歐美)市場(chǎng),秘訣還是得用自己本土的音樂。”“我一直堅(jiān)信,只有從自己民族和傳統(tǒng)文化中發(fā)掘出來的音樂,才能真正的影響世界。”帶著這種自主意識(shí),薩頂頂積極地從民族文化的原始宗教、民間音樂、鄉(xiāng)土音階中吸取養(yǎng)分,巧妙地將藏族、蒙古族、云南各少數(shù)民族的音樂風(fēng)格融匯一起,將質(zhì)樸的歌謠、獨(dú)特的民族樂器以及原生態(tài)的人生呈現(xiàn)了出來。在演唱風(fēng)格和舞臺(tái)妝扮上,薩頂頂也給我們呈現(xiàn)出瑰麗的民族特色和異域風(fēng)情,帶給聽者一種強(qiáng)烈的視覺震撼。她將民俗風(fēng)情元素推廣至廣闊的世界舞臺(tái),充分展示了東方的神韻之美。
再看現(xiàn)代西方元素。研究電子音樂元素一直以來都是薩頂頂?shù)呐d趣之一。薩頂頂首次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是在2000年的CCTV歌手大獎(jiǎng)賽,隨后她發(fā)行的專輯《自己美》,使她成為“中國第一電子女聲”。事實(shí)上,薩頂頂?shù)囊魳啡趨R了很多的現(xiàn)代西方元素,她把東方的音樂融進(jìn)西方的電子音樂,充分展現(xiàn)出民族的東西和產(chǎn)業(yè)化的制作結(jié)合所潛藏的無限生命力。在西方電子音樂元素的烘托之下,其音樂骨髓里的東方特質(zhì)得到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顯得更加出彩和現(xiàn)代。就像音樂制作人Tom Nichols所說:“……當(dāng)把她的嗓音和這樣的現(xiàn)代音樂形式,充滿了鼓點(diǎn),貝司、吉他和其他制作技術(shù)結(jié)合起來的時(shí)候,實(shí)在是非常酷,聽起來非常非常酷。”
不僅如此,薩頂頂?shù)膫€(gè)人樂隊(duì)也同樣充滿了多元的特質(zhì),不僅有歐美的電音器材,還有中國傳統(tǒng)的樂器。古箏、琵琶、馬頭琴、葫蘆絲、竹笛、蘆笙、鍵盤、電吉他、貝司、架子鼓等在薩頂頂?shù)囊魳分械玫搅送昝廊诤希纬梢还僧惓?qiáng)大的聽覺震撼,彰顯出薩頂頂不同尋常的多元化音樂風(fēng)格。對(duì)此,薩頂頂說:“我不拘束于任何一個(gè)音樂元素,不捆綁任何的單一文化,也許我的音樂蘊(yùn)涵著太多的文化信息,并且這些信息之中沒有唯一性和重復(fù)性,但我用這些已有的文化信息重新組建了自己的音樂體系,使得這些文化信息得到了重生的機(jī)會(huì),讓古老和現(xiàn)代糅合在一起,讓各個(gè)民族元素融合在一起,讓世界和中國聯(lián)系在一起,這就是我的音樂,這就是我獨(dú)特的處理音樂方式……”
五、結(jié)語
薩頂頂?shù)囊魳芬砸环N超功利的創(chuàng)作理念、深刻的精神內(nèi)涵、獨(dú)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和多元化的音樂元素,給當(dāng)代中國的流行音樂帶來了沖擊。這也使得“薩頂頂音樂”成為中國流行音樂史上最富于反叛性和開創(chuàng)性的具有開先河意義的新的音樂形式。其音樂所發(fā)生的影響,薩頂頂自己曾做過恰切的估價(jià):“我覺得是新東西對(duì)人心態(tài)的鍛煉,由于我的給予,觀眾的接受度會(huì)發(fā)生變化,不再以固有心態(tài)判斷和欣賞新東西;而很快也會(huì)有別人做不一樣的東西,然后形成一股風(fēng)潮,最終,中國流行音樂的整體得到改觀。”“如果沒有我,中國流行音樂應(yīng)該挺不多樣性的。”薩頂頂音樂創(chuàng)作的探索和實(shí)踐,不僅給當(dāng)代中國流行音樂的發(fā)展提供了參考,甚至給整個(gè)亞洲音樂的發(fā)展帶來啟迪。
需要指出的是,薩頂頂富于先鋒性意義的音樂極大地?cái)U(kuò)容了人們的音樂聽閾范圍,一旦這種特質(zhì)性的東西演變成為一種普遍性,如她所言“形成一股風(fēng)潮”了的話,那么人們是否還會(huì)帶著如此欣喜和驚奇的心情去期待和追捧?薩頂頂曾表示說,自己的第三張唱片“絕對(duì)不會(huì)再有地域元素了,我會(huì)再想出新的內(nèi)容”。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她的進(jìn)一步創(chuàng)新。另外,關(guān)于“自語”,薩頂頂表示這是一種很即興、很意外的偶然性音樂,而當(dāng)這種偶然性音樂反復(fù)被巡回演唱時(shí),它是否已經(jīng)僅僅成為了一種表演,而失卻了其本真的意義?然而不管怎么說,薩頂頂?shù)囊魳肥沟弥袊牧餍幸魳纷兊酶鼮樨S富和多元化,在整體上得到改觀,將中國的流行音樂推向了一個(gè)新的高度。
參考文獻(xiàn):
[1]梁銘越.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與中國音樂風(fēng)格的相關(guān)性[G]//中國音樂國際研討會(huì)論文集.濟(jì)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2]莊元.論流行音樂的三大基礎(chǔ)[J].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3).
[3]愛德華·漢斯里克.論音樂的美[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
[4]張世英.天人之際——中西哲學(xué)的困惑與選擇[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實(shí)踐與理論研究之路,幾近一個(gè)世紀(jì),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從整體上來看,中國現(xiàn)代音樂的理論研究是相對(duì)滯后于創(chuàng)作實(shí)踐的,并進(jìn)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傳播乃至價(jià)值認(rèn)定②。近年來,全國各大音樂學(xué)院紛紛成立了側(cè)重點(diǎn)略有不同,但都以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為任務(wù)的“中心”,這標(biāo)志著中國現(xiàn)代音樂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經(jīng)過相當(dāng)長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之后,開始了對(duì)這一歷史進(jìn)程進(jìn)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統(tǒng)、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理論研究新時(shí)期。武漢音樂學(xué)院中國現(xiàn)代音樂研究中心也正是順應(yīng)這一歷史潮流而成立的,并在成立之初就明確把成功舉辦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作為中心2005年度的最重要工作。
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的辦會(huì)思路,首先是為全國的作曲技術(shù)理論同行們搭建一個(gè)寬闊的研究中國現(xiàn)代音樂的平臺(tái),形成團(tuán)隊(duì)優(yōu)勢(shì),促進(jìn)隊(duì)伍發(fā)展,提高理論水平,促進(jìn)創(chuàng)作實(shí)踐;第二,有計(jì)劃、有步驟地邀請(qǐng)國內(nèi)外重要的華人作曲家,在年會(huì)期間舉辦與音樂創(chuàng)作實(shí)踐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講座,并與理論家及其理論研究形成直接與間接互動(dòng);第三,主辦單位武漢音樂學(xué)院與中心管理單位作曲系也希望通過年會(huì)的舉辦,有力地促進(jìn)本院、本系的音樂創(chuàng)作與理論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為年會(huì),表達(dá)了主辦單位與中國現(xiàn)代音樂研究中心希望能夠以長期不懈的形式,腳踏實(shí)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確定了“正式代表的論文宣講”、“嘉賓作曲家的主題講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論壇”以及“武漢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教師新作品音樂會(huì)”、“武漢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本科學(xué)生室內(nèi)樂作品音樂會(huì)”等主要內(nèi)容。
12月3日晚,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在武漢音樂學(xué)院編鐘音樂廳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式。會(huì)議齊聚了眾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論家,全國各音樂學(xué)院和多所藝術(shù)學(xué)院、師范大學(xué)、綜合大學(xué)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樂》《黃鐘》《長江日?qǐng)?bào)》《湖北日?qǐng)?bào)》、湖北衛(wèi)視等媒體的編輯記者。武漢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國現(xiàn)代音樂研究中心主任錢仁平宣布會(huì)議開幕。武漢音樂學(xué)院劉永平副院長主持開幕式,并宣讀了作曲界前輩羅忠先生、朱踐耳先生的賀辭。武漢音樂學(xué)院彭志敏副院長代表主辦單位向大會(huì)致辭。他代表東道主熱烈歡迎與會(huì)代表的到來,并強(qiáng)調(diào)這次會(huì)議是在積極調(diào)研、充分協(xié)商、廣泛征求同行的意見,并結(jié)合各方面條件和自身實(shí)際情況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這樣一個(gè)課題,選定了在第一次全國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huì)召開20周年這樣一個(gè)有意義的時(shí)間,并利用武漢音樂學(xué)院地處中部的地理優(yōu)勢(shì),為全國同行提供一個(gè)交流的平臺(tái)。武漢音樂學(xué)院前副院長匡學(xué)飛教授作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會(huì)的發(fā)起人之一也發(fā)表了講話,并對(duì)會(huì)議的召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還宣讀了武漢音樂學(xué)院前院長趙德義教授從海外發(fā)來的賀電。上海音樂學(xué)院徐孟東副院長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會(huì)致辭,并預(yù)祝會(huì)議成功。大會(huì)還收到了星海音樂學(xué)院院長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張千一博士以及中國音樂學(xué)院、西安音樂學(xué)院、首都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等兄弟單位的賀電。開幕式的最后,由武漢音樂學(xué)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楊鋒教授、天津音樂學(xué)院院長姚盛昌教授、上海音樂學(xué)院副院長徐孟東教授,為武漢音樂學(xué)院“中國現(xiàn)代音樂研究中心”揭牌。開幕式之后舉行了“武漢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教師新作品音樂會(huì)”。該場(chǎng)音樂會(huì)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其中不少作品為國際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國際、國內(nèi)獲獎(jiǎng)的優(yōu)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劉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圓之夜》――新笛、小堂鼓與八個(gè)音箱的十重奏和《風(fēng)的回聲》――為十六支中國大竹笛而作;黃汛舫教授的無伴奏女聲合唱《工尺譜游戲》;青年教師羅林卡創(chuàng)作的無伴奏女聲合唱《夜歌》;丁冰創(chuàng)作的《涉江序列變奏曲》――為兩把大提琴而作;章瓊創(chuàng)作的弦樂四重奏《華嚴(yán)?觀瀾》;馮堅(jiān)創(chuàng)作的《Soul.Wind》――為人聲與計(jì)算機(jī)而作;青年作曲家趙曦創(chuàng)作的《火天堂》――為小提琴與樂隊(duì)而作。本場(chǎng)音樂會(huì)由作曲系留美指揮博士周進(jìn)老師與2002級(jí)指揮專業(yè)本科學(xué)生黃勝華擔(dān)任指揮,武漢音樂學(xué)院管弦系、民樂系、聲樂系、演藝學(xué)院的師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年會(huì)“論文宣講”部分,在武漢音樂學(xué)院濱江校區(qū)學(xué)術(shù)會(huì)議中心舉行。武漢音樂學(xué)院中國現(xiàn)代音樂研究中心在大會(huì)召開之前印刷、裝訂了《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論文集》(責(zé)任編輯:錢仁平、張、黃茜、劉涓涓),并分發(fā)給參會(huì)代表。論文宣講第一場(chǎng)由首都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張大龍教授與上海音樂學(xué)院作曲指揮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漢音樂學(xué)院鄭英烈教授首先發(fā)言,他生動(dòng)地介紹了他與羅忠先生的結(jié)交以及共同深入學(xué)術(shù)研究的過程,并為年會(huì)呈獻(xiàn)了珍貴的《羅忠書信集》。藝術(shù)學(xué)院的李詩原副教授就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的研究現(xiàn)狀及研究方向作了相關(guān)發(fā)言。宣講論文的有上海音樂學(xué)院王瑞的《羅忠現(xiàn)代復(fù)調(diào)思維研究》、吳春福的《數(shù)以載樂,智以言情――析賈達(dá)群〈時(shí)間的對(duì)位〉結(jié)構(gòu)手法》、中央音樂學(xué)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樂合一――董立強(qiáng)為長笛、單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田文的《從全息角度探究〈土樓回響〉和聲運(yùn)用的規(guī)律性》、沈陽音樂學(xué)院周凌宇的《中西音樂素材及作曲技法結(jié)合的新型交響樂――楊立青的交響敘事詩〈烏江恨〉的創(chuàng)作分析》、中國音樂學(xué)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樂四重奏〉分析》、竹崗的《新的挑戰(zhàn),新的收獲――簡(jiǎn)析〈水賦三疊〉》等。
12月4日下午舉行了第二場(chǎng)論文宣講。本場(chǎng)論文宣講由中國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王寧教授、中國人民大學(xué)徐悲鴻藝術(shù)學(xué)院姜萬通副教授主持。王寧教授首先宣讀了中國音樂學(xué)院對(duì)大會(huì)的賀信。先后宣講的論文有武漢音樂學(xué)院張的《“微縮圖”式的引子及其“庫資源意義”――黃汛舫〈工尺譜游戲〉音樂分析》,劉涓涓的《線形化的表現(xiàn)手法――羅忠藝術(shù)歌曲〈鷓鴣天――彩綢殷情捧玉鐘〉JV56分析》,倪軍的《1985年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文獻(xiàn)綜述》,中國音樂學(xué)院溫展力的《樂譜的解放――“具體樂譜音樂”的引論》,武漢音樂學(xué)院云的《從三部作品來看劉健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電子音樂思維》,西安音樂學(xué)院陳士森的《〈二人臺(tái)〉全音階素材的運(yùn)用方式》,大連大學(xué)蔣興忠的《無調(diào)性音樂作品中和聲的整體控制作用――析羅忠〈鋼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蔡夢(mèng)的《李煥之新時(shí)期的器樂創(chuàng)作及其藝術(shù)特色》,武漢音樂學(xué)院錢仁平的《宏復(fù)調(diào)織體形態(tài)及其結(jié)構(gòu)功能――何訓(xùn)田〈聲音的圖案〉之三音樂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漢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本科學(xué)生室內(nèi)樂作品音樂會(huì)在編鐘音樂廳舉行,參加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的專家學(xué)者們與廣大觀眾一起饒有興趣地聽取了這場(chǎng)音樂會(huì)。音樂會(huì)演出的作品有王葉的鋼琴三重奏《京調(diào)托卡塔》、蔡建純的男高音與鋼琴《夜雨寄北》、姚娟的雙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孫劍的嗩吶與四聲道的五重奏《破陣圖》、劉丁的弦樂四重奏《我的詩篇》、王剛、張兢兢的《無序之槌》――為打擊樂與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與鋼琴、彭丹的《魅影》――為大提琴與計(jì)算機(jī)而作、何苗的鋼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時(shí),剛聽完“武漢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本科學(xué)生室內(nèi)樂作品音樂會(huì)”的全國各音樂學(xué)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齊聚一堂,召開了由武漢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發(fā)起的“第一屆全國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系主任聯(lián)席會(huì)”。參會(huì)者有中央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樂學(xué)院作曲指揮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樂學(xué)院音樂工程系副主任陳強(qiáng)斌、中國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王寧、沈陽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韻、四川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房曉敏、天津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顧之勉、首都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張大龍、副主任蔡夢(mèng)以及武漢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錢仁平。與會(huì)的系主任各抒己見,對(duì)全國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聲、曲式、復(fù)調(diào)、配器“四大件”的教學(xué)大綱、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形式、考試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設(shè)性的理念與構(gòu)想。大家還就各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師生之間的學(xué)術(shù)交流、資源共享等問題進(jìn)行了磋商。第一屆全國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主任聯(lián)席會(huì)最后決定,第二屆聯(lián)席會(huì)將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舉行。
12月5日上午,年會(huì)之“嘉賓作曲家主題講座”暨武漢音樂學(xué)院“新世紀(jì)音樂論壇”第四期、第五期在編鐘音樂廳相繼“開壇論道”!首先登上論壇的是作曲家、中央音樂學(xué)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題目是《交響詩〈川崖懸葬〉――為兩架鋼琴與管弦樂隊(duì)而作――的音高組織》。郭文景首先簡(jiǎn)要回顧了這首作品的選題原因及其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隨后從和聲、調(diào)式和音階三個(gè)方面對(duì)《川崖懸葬》的音高組織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闡釋。上海音樂學(xué)院副院長、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徐孟東的論題是《上海音樂學(xué)院作曲家群體近年來的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綜述》。他首先論述了上海對(duì)于中國現(xiàn)代音樂發(fā)生、發(fā)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xiàn),接著對(duì)上海音樂學(xué)院作曲家群體近年來在創(chuàng)作觀念、技法方面的思考、變化與突破,進(jìn)行了簡(jiǎn)略論述。他指出上海音樂學(xué)院作曲家群體回歸了“海派”音樂文化的特征,并統(tǒng)一匯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納百川――的潮流之中。他還進(jìn)一步指出,上海音樂學(xué)院作曲家群體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音樂,在觀念層面上體現(xiàn)出“復(fù)合風(fēng)格”。各種現(xiàn)代技法為我所用,創(chuàng)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國現(xiàn)代音樂作品。他們?cè)趧?chuàng)作音樂的過程中,力圖創(chuàng)作的音樂保持中國音樂的“神韻”,在作品中又運(yùn)用了大量的現(xiàn)代音樂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隨后,他還對(duì)何訓(xùn)田的室內(nèi)樂《聲音的圖案》、賈達(dá)群《蜀韻》、尹明五的舞劇音樂《憶》、他自己的《驚夢(mèng)》以及葉國輝的《聲音的六個(gè)瞬間》、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陳強(qiáng)斌的《飛歌》進(jìn)行了簡(jiǎn)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舉行了第三場(chǎng)論文宣講。本場(chǎng)論文宣講由天津音樂學(xué)院作曲系副主任顧之勉副教授、上海音樂學(xué)院音樂工程系副主任陳強(qiáng)斌副教授、藝術(shù)學(xué)院李詩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講的論文有中央音樂學(xué)院婁文利的《瞿小松室內(nèi)歌劇〈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漢音樂學(xué)院田可文的《讀〈月的悲吟〉》、鄭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復(fù)調(diào)形態(tài)的計(jì)算機(jī)模擬》、汪森的《關(guān)于現(xiàn)代音樂的本體論思考》,首都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馮蘭芳、盧璐的發(fā)言,西安音樂學(xué)院夏滟洲的《現(xiàn)代音樂還是應(yīng)該建立在可聽的基礎(chǔ)之上》以及中國人民大學(xué)姜萬通的《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系統(tǒng)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舉行了由特邀代表輪流發(fā)言的“自由論壇”。論壇由中國現(xiàn)代音樂研究專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會(huì)發(fā)起人之一、首都師范大學(xué)王安國教授主持。中國音樂學(xué)院高為杰教授首先就音樂創(chuàng)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賞”這個(gè)議題和大家進(jìn)行了深入的探討。他認(rèn)為作曲家既要能創(chuàng)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樂,又要能創(chuàng)作出面向大眾的“俗”音樂,要能把雅文化與俗文化更好地結(jié)合起來。他以皮亞佐拉的“新探戈”為例進(jìn)行了論述。接著他還給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臺(tái)灣城市民謠創(chuàng)作的樂曲,這部作品中“夾雜”了《流浪者之歌》《瑤族長鼓舞》《劍之舞》等曲調(diào),但在配器上運(yùn)用了獨(dú)特的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手法,給聽眾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達(dá)到了雅俗共賞的目的。高為杰教授最后指出,實(shí)際上要達(dá)到雅俗共賞是十分困難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論功底、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yàn)以及深厚的文化修養(yǎng)。中國音樂學(xué)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師們?cè)诮虒W(xué)中應(yīng)該不拘一格培養(yǎng)人才,并建議將包括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在內(nèi)的現(xiàn)代音樂課程納入音樂院校的教學(xué)體系中去,以便讓同學(xué)們對(duì)現(xiàn)代音樂有更全面的認(rèn)識(shí)與了解。天津音樂學(xué)院院長姚盛昌教授就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如何做到“得心應(yīng)手”、“得手應(yīng)心”與“心手相應(yīng)”,作了發(fā)言。金湘、房曉敏、張大龍、楊青、曹家韻、宋名筑、鄭英烈、劉健等分別就如何面對(duì)和解決作曲教學(xué)、理論研究、音樂創(chuàng)作中所存在的不足與問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由“自由論壇”不間斷地過渡到簡(jiǎn)短的閉幕式。彭志敏副院長代表主辦單位講話,他指出這次會(huì)議的成功召開,對(duì)中國現(xiàn)代音樂今后的發(fā)展,將起到積極和深遠(yuǎn)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歡迎各位專家學(xué)者繼續(xù)傳經(jīng)送寶,共同推動(dòng)中國現(xiàn)代音樂的發(fā)展。會(huì)議最后,主持人王安國教授發(fā)表了感情深厚的結(jié)束語,對(duì)武漢音樂學(xué)院長期以來致力于現(xiàn)代音樂、中國現(xiàn)代音樂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及其對(duì)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發(fā)展所起到的促進(jìn)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與會(huì)代表對(duì)武漢音樂學(xué)院的富有成效的會(huì)務(wù)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謝。
讓我們共同努力,為中國現(xiàn)代音樂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與理論研究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做出新的應(yīng)有的貢獻(xiàn)。
①魏廷格《武漢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huì)綜述》,《中國音樂學(xué)》1986年第2期;李曦微《新音樂的思索》,《中國音樂學(xué)》1986年第2期;汪申申、劉健、周晉民《新時(shí)代呼喚著新的音樂》,《人民音樂》1986年第3期;李詩源《新潮音樂備忘錄――1979-1999年的中國大陸現(xiàn)代音樂》,武漢音樂學(xué)院中國現(xiàn)代音樂研究中心編《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huì)論文集》,武漢音樂學(xué)院2005年12月油印等相關(guān)文獻(xiàn)。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huì)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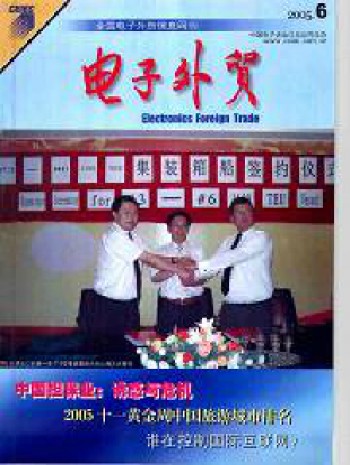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jí)期刊
中國電子進(jìn)出口總公司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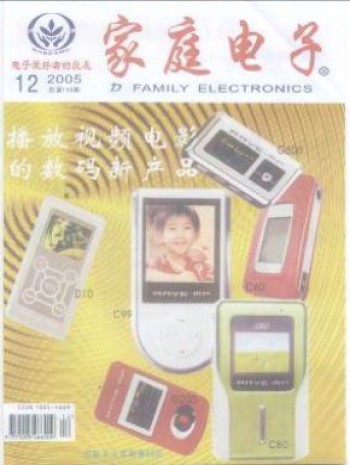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四川省科學(xué)技術(shù)廳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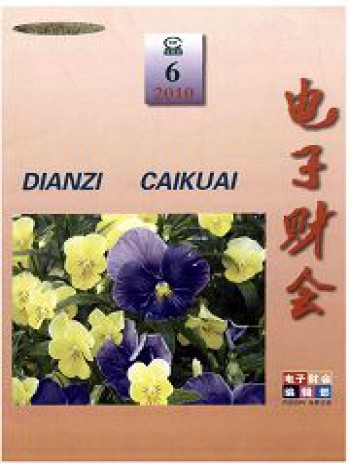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信息產(chǎn)業(yè)部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與經(jīng)濟(jì)運(yùn)行司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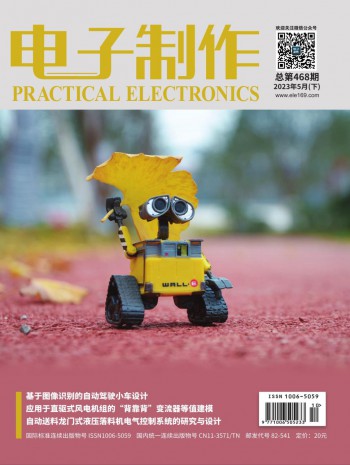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jí)期刊
中國商業(yè)聯(lián)合會(huì)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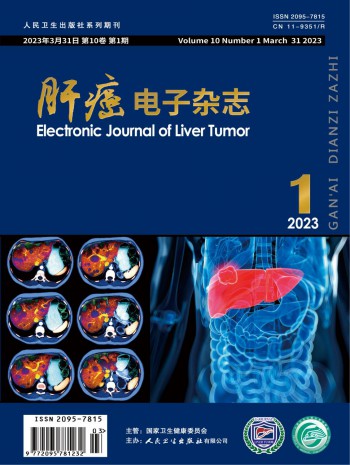
預(yù)計(jì)1-3個(gè)月審稿 統(tǒng)計(jì)源期刊
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huì)主辦